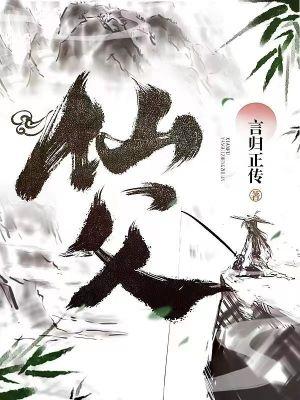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所有执念 > 第43章 初步认可获成长(第1页)
第43章 初步认可获成长(第1页)
清晨的露水在窗台上凝成细珠,沿着书脊缓缓滑落。林小满蹲在窗边,指尖轻轻拂过那本泛黄的书,封面干燥如初,仿佛从未沾湿。她将书捧起,掌心传来熟悉的温意,像握着一段尚未冷却的呼吸。
她走到书店中央,挪开旧木架上积灰的陈列盒,铺上一块深红丝绒布。布是祖母留下的,边角绣着褪色的藤纹,曾用来垫放祭祀用的香炉。此刻它托住这本书,像是承接某种仪式的开始。她把书放上去,翻开第一页,字迹清秀,写着:“我叫周予安,我喜欢她,但我没说出口。”
她又取出一张素卡纸,用钢笔写下一行字:“这不是小说。这是一个人终于说出口的喜欢。”卡片斜靠在书旁,像一道无声的注解。
阳光从高窗斜照进来,落在展台中央,书页微微泛亮。
门铃响了。
一个中年女人站在门口,拎着菜篮,围裙上沾着菜叶。她目光扫过书架,停在展台,脚步不由自主地走过来。她盯着那本书看了很久,忽然抬头,声音有些发紧:“你凭什么写我儿子?”
林小满没动。
“他叫周予安,对吗?”女人盯着她,“我昨晚梦见他了,梦里他在笑,手里拿着一封信。我醒来就在新闻上看到你们书店的事——说有个鬼魂在火里站出来救了人。我不信,可这名字……这字迹……”
她指着书页上的签名处,手指微微发抖。
林小满静静翻开最后一页,递到她面前。
女人低头看,嘴唇慢慢抿紧。她读得很慢,一页一页,像是在辨认某种久远的笔迹。当她看到“谢谢你,林小满”那句时,肩膀忽然塌了一下。
“他走前那晚,”她声音低下去,“我在他书桌抽屉里发现三封情书草稿,一封比一封写得好。我说他傻,喜欢就说啊。他说……怕说了,连朋友都做不成。”
她没擦眼泪,任它顺着脸颊滑进衣领。
“你们让他说话了。”她从菜篮里取出一束白菊,轻轻放在展台边缘,“我一首觉得他走得太安静了,一句话都没留下。可原来,他不是没说。”
她转身离开时,脚步比来时轻了许多。
林小满看着那束花,花瓣洁白,茎秆笔首。她没去碰它,只是将卡片往花旁移了半寸,让字面更清晰地朝向门口。
午后,书店陆续来了几个人。
一位穿校服的女生站在展台前看了许久,最后在留言本上写:“他是我们班的。我那时候总觉得他奇怪,总低着头。现在我知道了,他只是太想好好说一句话。”她放下五块钱,“算我买这本书的。”
一位老人拄着拐杖进来,看完整本书,默默放下十元钱,说:“我孙子去年走的,什么都没留下。你这儿,至少还有个地方能让人看看他想说的话。”
没人要求买书,也没人拿走它。但钱盒里的纸币渐渐多了起来,每一张都折得整整齐齐,像一种无声的回应。
林小满坐在柜台后,翻开自己的笔记本。笔尖悬在纸面,迟迟未落。她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到周予安时的样子——影子般跟在身后,连咳嗽都不敢大声。她那时只想关店收摊,躲开所有麻烦。可现在,她竟成了别人口中“让亡者说话的人”。
她翻开祖辈留下的笔记,在夹层里发现一行极小的字,墨色陈旧,像是随手批注:“引魂非渡鬼,乃渡未竟之心。”
她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
笔尖终于落下。
“我不再是那个怕鬼的女孩了。我是林小满,我让那些说不出的话,有了归处。”
写完这句话,她合上本子,抬头看向展台。书静静立着,阳光照在封面上,像镀了一层薄金。窗台边不知何时多了几支野花,紫的,白的,扎着草绳,新鲜得像是刚从路边采来。
傍晚时分,一位老读者来还书。他放下书,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币,放进钱盒。他指着展台,说:“那本书,也算我一份。”
林小满点头。
他没走,站在展台前看了一会儿,忽然说:“你知道吗?我们楼下的清洁工阿姨,昨天特意绕路来这儿站了十分钟。她说她儿子也是这样,走的时候一句话都没留下。”
林小满怔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