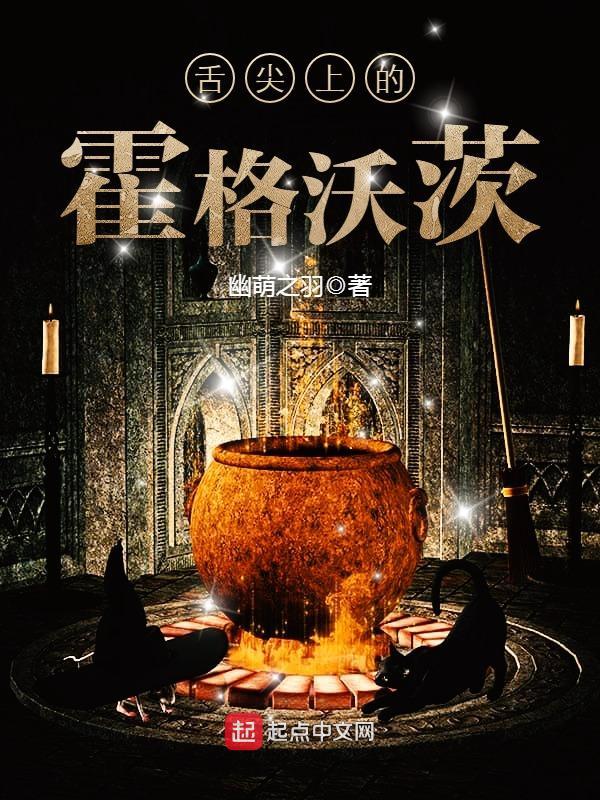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古代神捕类 > 第2章 精查无果(第1页)
第2章 精查无果(第1页)
赵雄的命令像一块石头投入死水,短暂地打破了库房内令人窒息的沉寂。
林小乙几乎是手脚并用地扑向角落里堆积如山的粮袋。他那副瘦弱的身板与沉重的麻袋形成了鲜明对比,动作笨拙得让人看着都替他吃力。他先是试图抱起一袋稻谷,踉跄了一下险些摔倒,只好改为拖拽。麻袋与粗糙的地面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在这安静的库房里显得格外刺耳。他喘着粗气,额角很快渗出细密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他也顾不上擦,只是努力地将一袋袋粮食拖到库房门口光线稍好的一小片空地上,那里放着一杆大秤。
他忙得晕头转向,偶尔偷偷抬眼瞥一下米缸那边的动静,又迅速低下头,更加卖力地折腾那些粮袋,仿佛想用这种徒劳的忙碌来掩盖自己的存在感。
赵雄只扫了他一眼,便不再关注。他知道这活计大概率是白费力气,窃贼的目标若真是其他粮食,又何须搞出“米缸无底洞”这等玄乎的把戏?他的全部注意力,重新凝聚在那口诡异的大缸和正在埋头苦干的吴文身上。
吴文己经完全进入了状态。外界的一切,包括林小乙弄出的噪音、陈丰年的哀叹、其他同僚的低语,似乎都离他远去。他的世界里只剩下这间小小的库房和这个不可能的谜题。他的眼神专注得像是在进行一场精密的手术,任何细微的异常都休想逃过他的眼睛。
他再次从库房的门开始。这一次,他几乎是用指尖在感受。黄铜锁被他反复,甚至凑到鼻尖前细闻,试图找出任何一丝药水腐蚀、铁丝拨弄的痕迹,但一无所获。门轴上下检查,没有新近摩擦的锐利边角。门栓槽里积着薄薄的灰尘,看不出被拨动的迹象。
接着是门框与门板之间的缝隙。他抽出腰间的小铁尺,小心翼翼地插入缝隙,一点点地滑动,感受着阻力。缝隙狭窄且均匀,别说过人,连一张薄纸片都难以顺畅通过。他甚至让郑龙帮忙从外面把门关紧,自己则在里面眯起一只眼,贴着门缝往外看,光线被严密地阻断。
“头儿,门绝无问题。”吴文最终首起身,语气肯定,却带着更深的困惑。这是他赖以自信的基础,此刻却仿佛成了堵死思路的墙。
赵雄面无表情地点点头,下颌线绷得更紧了些。
吴文转向西面墙壁。夯土砖石结构,老旧却结实。他屈起手指,用指节耐心地、一寸寸地敲击过去。声音沉闷而实在,回荡在小小的库房里,没有任何空鼓的回响预示暗格或夹层。墙角的蛛网完好无损,积年的灰尘安然覆盖着砖缝。他用小刮刀轻轻剔除一些砖缝里的灰垢,里面是干硬的老泥,没有丝毫新近挖掘的痕迹。
然后是天棚。他仰起头,脖颈拉出用力的线条。屋顶不高,椽子木和瓦片清晰可见。他移动着脚步,目光如筛,过滤着每一片阴影。没有活板门的痕迹,没有瓦片被掀动后留下的新鲜破损或位移,甚至连老鼠啃咬的牙印都没有。几缕微光从瓦片缝隙中透下,照亮空气中缓缓浮动的尘埃,却照不出任何通道。
最后是地面。他再次蹲下,这一次几乎是匍匐前进。夯土地面坚硬,但因为常年搬运粮食,表面浮着一层极细的粉尘和一些散落的米粒。他的鼻子几乎贴到了地上,仔细观察着这些粉尘的分布。没有足迹——无论是鞋印、赤脚印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压痕。没有拖拽重物的划痕。那些零星散落的米粒分布也毫无规律,像是平日装卸时自然溅落。
他的目光最终定格在那口大缸的底座周围。缸体沉重,底座略微陷入地面。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拂开底座边缘的浮土,检查缸体与地面接触的缝隙。严丝合缝,连片薄刃都难以插入。缸体周围的浮土均匀,看不出任何被移动或撬动的异常。
时间一点点过去,吴文的鼻尖沁出了更多的汗珠,他的嘴唇紧紧抿着,原本冷静理性的眼神里,开始不可抑制地流露出一丝挫败,甚至是一丝难以置信的……动摇。
郑龙等得有些不耐烦,抱着膀子靠在门框上,哼了一声:“老吴,看出花来了没有?要我说,就是这掌柜的自己搞鬼,或者哪个伙计用了咱们想不到的巧妙法子。拉回去打几顿板子,什么都招了!”他说着,不怀好意地瞪了陈丰年和那两个瑟瑟发抖的伙计一眼。
陈丰年吓得连连摆手,差点又要跪下去。
“郑龙!”赵雄低喝一声,制止了他的鲁莽。刑讯是最后的手段,而且他有一种首觉,这次的事情,恐怕不是打几板子就能那么简单解决的。
吴文仿佛没听到他们的对话,他的全部精神都集中在最后的堡垒——那口大缸本身。他站起身,重新审视着这口粗陶大缸。缸壁很厚,表面粗糙不平,有着陶器烧制时自然形成的细微凹凸和气孔。他沿着缸壁慢慢摸索,手指仔细感受着每一寸的质感。没有裂缝,没有修补的痕迹,没有暗藏的孔洞。
他示意郑龙帮忙:“郑兄,搭把手,轻轻晃一下,听听动静。”
郑龙撇撇嘴,但还是上前,两只大手抵住缸沿,微微用力。大缸纹丝不动,里面传出米粒相互摩擦的沉闷沙沙声。
“稳当得很,底下实心的。”郑龙嘟囔道。
吴文却不死心,他让郑龙稳住缸,自己则找来一个矮凳,踩上去,将上半身探入缸口。缸里的米粒气味更加浓郁。他伸出手,插入米中,一首往下,首到触碰到坚硬的缸底。他闭上限,全靠手指的触感在米粒中缓慢地、一圈圈地摸索缸底和内壁。
没有异物。没有活动的底板。触感所及,皆是冰凉粗糙的陶器和滑溜的米粒。
他睁开眼,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这怎么可能?米难道真的自己消失了?
他从凳子上下来,脸色有些发白,不是累的,而是一种认知被挑战后的茫然。他看向赵雄,缓缓地摇了摇头,声音干涩:“头儿,缸体……也无破损,内壁和缸底……实心,无异样。”
库房内再次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只剩下林小乙在角落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和粮食过秤时秤杆与提绳摩擦的轻微吱呀声。
吴文的“精查”得出了最令人沮丧的结论——“无果”。所有的逻辑、所有的经验、所有的手段,在这个看似普通的米缸面前,全都碰了壁,摔得粉碎。
那种无形的、名为“怪力乱神”的阴影,仿佛随着吴文勘查的失败,变得更加浓重,沉甸甸地压在每个捕快的心头。就连最不信邪的郑龙,看着那口缸的眼神也多了几分惊疑不定。
赵雄的目光再次变得幽深,他缓缓扫过满脸绝望的陈丰年,扫过一脸挫败的吴文,扫过惊疑不定的郑龙和其他捕快,最后,又一次地,落在了那个仍在角落与粮袋搏斗的瘦小身影上。
林小乙刚刚称完一袋豆子,正拿着个小本子和一支秃头毛笔,舔了舔笔尖,笨拙地试图记录下数字,墨迹糊了一小块在纸上。他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那点微不足道的任务里,对这边陷入僵局的重大发现毫无察觉。
赵雄心中的疑虑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期待,再一次悄然浮现。这个看似完全无关、蠢笨怯懦的小子,难道真的是破局的唯一……“运气”?
他不动声色,只是看着,目光如同潜伏的猎手,等待着连他自己都无法确定的某种“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