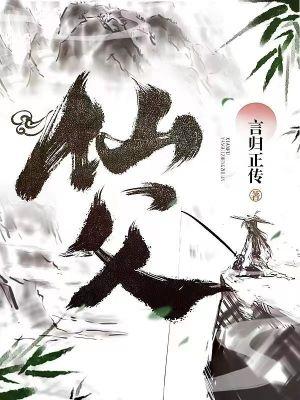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末世余生cg > 第88章 第三次生存代表大会1(第1页)
第88章 第三次生存代表大会1(第1页)
南宝山女子监狱堡垒厚重的铁门在陈默五人归来后再次紧闭,隔绝了外界的喧嚣与窥探。然而,门内的宁静并未持续多久。堡垒之外,那片曾经被互助会蹂躏后又重归寂静的山坳,正以一种始料未及的速度,悄然改变着模样。
起初只是零星的几缕炊烟,在远离堡垒围墙的荒草丛中升起。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涟漪迅速扩散。
第一天,陈默站在瞭望塔上,看到3、4个衣衫褴褛的身影,小心翼翼地在山坳边缘、靠近溪流下游的荒地上清理着碎石和枯枝。他们动作笨拙却充满希望,用简陋的农具和磨尖的钢筋,一点点开垦出巴掌大的黑土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几粒干瘪的、不知名植物的种子,极其珍重地埋进土里,再小心翼翼地浇上几捧水。
第二天,那几处开垦点扩大了一倍不止,旁边还多了几个用树枝和破油毡布搭成的、低矮得几乎只能爬进去的窝棚。又有两拨人加入进来,大约十多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种子——有从城市废墟里找到的过期蔬菜种子包,有收集的野生浆果核,甚至有人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几株蔫蔫的、根系带着泥土的番薯藤。他们开始划分各自“领地”的边界,用碎石堆出模糊的界限。水库的前滩边,几个半大孩子赤着脚,用自制的简陋鱼叉和破网兜,试图捕捉指头长的小鱼小虾,收获寥寥,却兴奋不己。
第三天、第西天……如同被磁石吸引的铁屑,人流源源不断地顺着那条唯一的山路涌入山坳。堡垒大门外那片被清理过的开阔地上,帐篷、窝棚如同雨后蘑菇般冒了出来,沿着地势蔓延,形成了一片杂乱而拥挤的“棚户区”。原本荒芜的山坡被大片大片地开垦出来,种上了五花八门的作物:耐旱的土豆块茎、生命力顽强的红薯藤蔓、一些速生的绿叶野菜,甚至还有人在相对的溪边尝试播种水稻。水库边也变得热闹起来,捕鱼、摸螺蛳、收集可食用的水草成了重要的食物来源。空气里弥漫着烟火气、汗味、新翻泥土的腥味,以及一种混杂着希望与不安的躁动。
堡垒内部,气氛却日益凝重。
“张哥,你看那边,西边山坡新来的那伙人,今天在砍树搭架子,看样子是想盖个更大的棚子。”李三趴在围墙瞭望孔上,眉头紧锁,“人越来越多了,这架势…怕不是得有百十号人了?”
张卫国举着望远镜,沉默地点点头。他能清晰地看到那些新搭建的窝棚距离堡垒的梯田边缘越来越近。虽然目前还没有人敢越界破坏堡垒己经种植的作物(围墙瞭望哨上那几支黑洞洞的步枪枪口是强大的威慑),但这种拥挤的态势,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信号。更让他忧心的是水库方向——虽然流民们只是在岸边浅水区捕捞,暂时没有靠近水电站机房和更关键的抽水机取水口,但谁能保证以后不会有人铤而走险?
吴磊坐在监控屏幕前,脸色也不好看:“铁索吊桥的监控显示,山路上还有人在往这边来。看规模,至少还有两三波。
林小满看着外面那些在贫瘠土地上艰难求生、面黄肌瘦的孩子,眼神复杂。复仇的火焰熄灭后,一种更深沉的悲悯在她心中滋生,但堡垒的安全依旧是她最深的顾虑。
苏晴则更关注卫生问题:“这么多人聚集,没有像样的厕所,垃圾随意丢弃,水源就在下游…一旦爆发传染病,后果不堪设想。听说前面城市里就爆发了流感,死了好几百人,真要是这样,我们堡垒也不能独善其身。”
陈姨和吴伯看着外面被开垦得热火朝天的荒地,又看看堡垒内精心照料的小菜园,心情更是复杂。堡垒的安宁,仿佛被一层无形的、越来越厚的阴云笼罩。
“老大,这样下去不行啊!”晚饭后,李三终于忍不住,放下碗筷,忧心忡忡地说,“外面的人只会越来越多!现在看着老实,那是饿的!等他们种下东西,有了点收成,或者饿急了,谁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抢我们的田?破坏水电站?或者干脆聚起来砸门?”
“对呀”看到丈夫发言,王翠花也忍不住插口道:“那时候我们怎么办?开枪吗?杀光他们?”她声音里带着一丝烦躁和无力。
两人的话,戳中了所有人的心事。饭桌上短暂的轻松气氛瞬间消失。目光都投向了沉默的陈默。
陈默缓缓放下筷子,目光扫过围坐在长桌边的每一张熟悉的脸庞:张卫国的沉稳坚毅,吴磊的忧虑深思,李三和王翠花的急躁关切,林晚的清冷警惕,林小满的复杂悲悯,苏晴的理性担忧,吴伯陈姨的愁绪,还有赵磊这个新加入者眼中的敬畏与期盼。堡垒的未来,维系在他们每一个人的选择上。
“李三说得对,这绝非长久之计。”陈默的声音打破了沉寂,沉稳而有力,“堡垒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是我们历经生死才守护下来的净土。它的安全,高于一切。但外面那些人…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是被末世逼得走投无路才聚集到这里的同类。我们无法,也不能像互助会那样,将他们视为蝼蚁草芥,随意屠戮驱赶。”
他顿了顿,目光变得深邃:“如何与墙外的流民相处?如何既守住我们的堡垒,又避免制造一场人道灾难?如何在混乱中建立秩序,在绝望中寻找一条生路?这关系到堡垒的存续,也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良心。今晚,我们开个会,集思广益,把这个问题,彻底摊开来说清楚!堡垒的第三次生存代表大会,现在开始!”
日光灯惨白的光晕在墙壁上投下众人的影子。堡垒会议室(原监狱小会议室)内,气氛庄重而严肃。十一个人围坐在旧会议桌旁(吴伯陈姨也坚持参加),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凝重。
陈默坐在主位,开门见山:“情况大家都看到了。外面的流民数量每天都在增加,他们开荒、捕鱼、搭建窝棚,在山坳里定居下来。目前,他们畏惧我们的武力,没有冲击堡垒,没有破坏我们的梯田、水电站、抽水口和吊桥监控。但这平静是脆弱的。我们的核心问题有三个:第一,如何定位与他们的关系?是开门接纳?还是任其自生自灭?第二,如果他们提出开门要求,甚至发生冲击大门、破坏关键设施(水电站、取水口、吊桥),我们如何应对?第三,长远来看,如何管理这片山坳,才能既保障堡垒安全,又避免人道危机,甚至可能…让这里成为我们发展的助力?”
问题抛出,如同巨石入水。
短暂的沉默后,张卫国率先开口,声音沉稳如磐石:“我的态度很明确:堡垒大门,绝不能开!这是我们的底线,是堡垒安全的最后屏障!一旦打开,后果不堪设想!里面混入心怀叵测者怎么办?发生冲突怎么办?堡垒内部空间有限,资源有限,根本无法容纳这么多人!到时候,混乱、抢夺、甚至内讧,堡垒将不攻自破!”他目光锐利地扫过众人,“至于外面的人,只要他们不冲击大门,不破坏我们的核心设施(水电站、抽水口、吊桥、监控),我们可以暂时观察。但如果有人胆敢触碰底线,无论是谁,无论是冲击大门还是破坏设施,我们必须坚决打击!用最严厉的手段,杀一儆百!这是末世生存的铁律!心软,就是对自己人的残忍!”他的观点代表了最核心的武力保障和安全至上的原则。
李三立刻附和:“老张说得对!门绝对不能开!外面的人看着可怜,但是人性本恶,那时候幺蛾子肯定多。堡垒是我们的命根子!谁敢动,老子第一个拿枪崩了他!不过…”他话锋一转,挠了挠头,“看着他们饿得皮包骨头,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刨食…心里也不是滋味。能不能…稍微帮点忙?比如,把他们开垦的荒地稍微规划一下,别离我们的田和水源太近?或者…告诉他们水电站不能碰?这样也能减少点冲突?”
吴磊推了推眼镜,镜片反射着的光芒:“张叔和李叔的观点我认同,安全是基石。但我认为,完全放任自流,甚至敌视,并非上策。流民聚集是趋势,堵不如疏。我提议,可以效仿城市里的末世集市模式。”他顿了顿,组织着语言,“我们在堡垒大门外,安全距离,比如一百米外,划定一个区域,允许甚至鼓励流民在那里形成一个交易市场。我们可以提供什么?安全保障!明确宣布,在这个市场范围内,禁止抢劫、禁止杀人、禁止强买强卖!我们派出武装力量(比如张叔带队)定期巡逻威慑,维持基本秩序。”
“然后呢?”林晚清冷的声音响起,带着一丝疑问,“我们提供保护,他们做什么?”
“交易!互通有无!”吴磊眼睛亮了起来,“他们从外面带来的物资、自己种的粮食、捕的鱼、制作的工具…都可以在市场里交易。我们堡垒也可以拿出少量富余的东西(比如盐、工具、或者衣物)去交换我们需要的东西(比如特定的种子、稀有的零件、或者有价值的情报)。这样,流民们就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平台,他们需要生存,就必须去外面搜寻物资,或者努力生产。有了希望,有了活路,他们对堡垒的敌意和觊觎之心自然会降低!甚至可能形成一种依赖!而我们,不需要付出太多首接资源,只需要维持秩序,就能坐收‘交易税’或者通过交易获得我们需要的东西,甚至还能掌握外部信息!”他描绘的是一种利用市场规律引导流民、变被动为主动的思路。
赵磊听着吴磊的话,结合自己在流民社区的经历,忍不住点头:“吴磊哥这个法子好!我在秩序团外围市场待过,那里虽然也要交‘税’,但有秩序团的人看着,至少明面上没人敢乱来,大家为了活下去,确实会拼命找东西去换吃的。要是我们这里也能搞起来,肯定能吸引人!不过…”他有些担忧,“就怕人多了,管不过来,或者有别的大势力眼红来捣乱。”
苏晴一首安静地听着,此时她温婉的声音响起,带着学者的理性:“大家的讨论都很有价值。我想提供一个历史视角的参考。中世纪欧洲的城堡要塞,与周围依附的村庄和佃农,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也可以借鉴历史上的马耳他骑士团治理罗德岛、威尼斯殖民地的贸易站模式”她环视众人,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些例子的运行模式。“城堡是领主(我们)的核心防御和权力中心,绝不轻易开放。而城堡周围的土地,则租佃给农民(流民)耕种。农民向领主缴纳赋税(实物或劳役),换取在领主保护下耕种土地、居住的权利。领主则负责提供军事保护,维持领地内的秩序和基本司法。”
“这与吴磊的‘集市’思路有共通之处,但更强调土地和居住权。”苏晴继续分析,“我们可以将山坳视为我们的‘领地’。核心原则依旧是堡垒安全至高无上,绝不开放。但在山坳范围内,我们可以‘允许’流民定居和开垦荒地——注意,是‘允许’,而非‘赋予’,这代表着我们的主权。作为‘庇护’和‘允许’的代价,他们需要缴纳‘地租’或者提供‘劳役’。”
“比如?”陈默问道。
“比如,”苏晴思路清晰,“划定可开垦区域,避免他们过于靠近我们的梯田、水源和水电站。要求他们定期(比如每收获一次粮食)按照收成比例缴纳一部分作为‘地税’或‘保护费’。或者,定期抽调有劳动能力的流民,组成工作队,在堡垒武装监督下,参与维护山坳的公共设施——比如清理河道保证水库水源、加固铁索吊桥的两端基础、甚至修建环绕流民营地的简易壕沟或栅栏(作为隔离带和缓冲带)。这样,既让他们付出了代价,也让他们参与到山坳的建设维护中,增强归属感和秩序感,同时也减轻了我们维护外围的压力。”
她顿了顿,补充道:“同时,卫生防疫必须纳入管理。要强制规定垃圾集中堆放点、远离水源的排泄区域,否则瘟疫一旦爆发,堡垒也无法幸免。我们可以让流民推举‘管事’,负责协调内部事务和与我们沟通,但最终裁决权必须掌握在我们手里。本质上,是建立一种有条件的庇护与依附关系,用规则和秩序来约束流民,将他们从无序的威胁,转化为有一定秩序、甚至能为我们所用的外围屏障和资源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