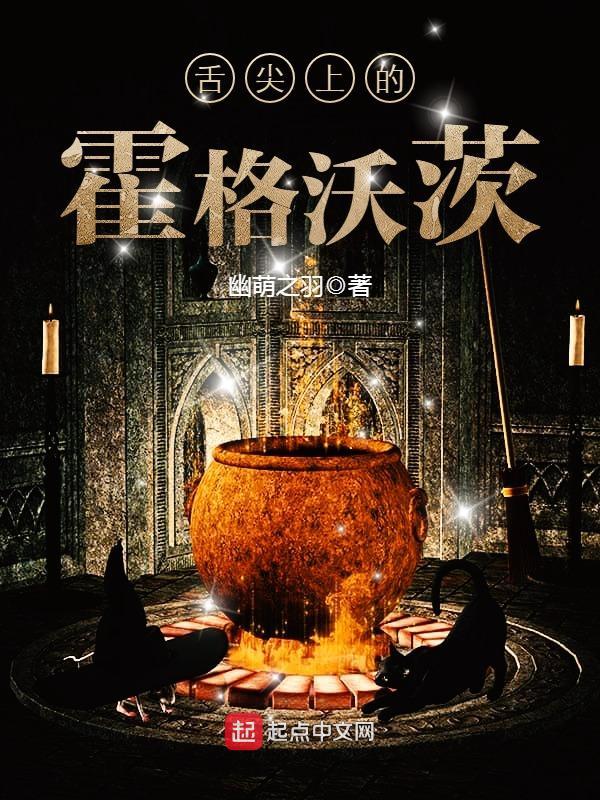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朕唐武宗开局在仇士良刀尖躺平 > 048鱼弘志 我挽大厦之將倾(第1页)
048鱼弘志 我挽大厦之將倾(第1页)
韩国公府,鱼弘志的书房內,昂贵的波斯绒毯上,散落著几片被撕碎的纸屑和一个歪倒的笔筒——显然是主人盛怒之下的杰作。
而我们的韩国公鱼弘志呢?此刻他肥胖的身躯在房中焦躁地来回踱步,脸上早已没了白日的得意,只剩下惊惶、悔恨和后怕交织的惨白。
仇士良那番看似平和、实则字字诛心的警告,如同毒蛇般缠绕在鱼弘志心头,让他坐立难安,嘴里也在无意识地念叨著“完了,完了。”
“蠢货,莽夫,得意忘形。”鱼弘志猛地停下脚步,先懊悔地低吼一声,隨后抬手狠狠给了自己两个响亮的耳光。
清脆的响声在寂静的书房里格外的响,脸颊上顿时浮现出清晰的指印。
鱼弘志捂著脸,脸颊上火辣辣的疼痛,同时觉得脑中一片混乱,嗡嗡作响。
“叫你得意忘形,叫你被那点权势冲昏头,叫你去捋那老疯狗的虎鬚。”鱼弘志打完自己片刻后又低吼了一声。
鱼弘志越想越怕,仇士良的手段他是知道的,那老狗绝不会善罢甘休。
自己这一步,究竟是登天梯,还是鬼门关?
鱼弘志烦躁地抓著头,感觉脑子里一团浆糊,越想理清思路越是混乱。
不行,不能坐以待毙。
“来人。”鱼弘志嘶哑著嗓子对著门外低吼道:
“立刻,马上,去把张承禄、邓先生,还有王都头、李押衙,都给咱家叫来,立刻,不管什么时辰,快去。”
鱼弘志此刻已顾不得宵禁,以他的权势,深夜召见心腹,无人敢拦。
很快,几名心腹被从府中各处紧急召来,包括都押衙张承禄,以及他府中唯一的智囊、以幕僚身份依附的清客邓宇哲。
书房內,烛火通明。
鱼弘志脸色灰败,將今日紫宸殿外仇士良那番话,以及自己此刻的担忧、甚至那一丝悔意,都竹筒倒豆子般说了出来。
鱼弘志竹筒倒豆子般將今日如何奉旨调兵入宫接手防务,如何在紫宸殿外被仇士良敲打的经过,原原本本复述了一遍,尤其强调了仇士良话语中的威胁和自己此刻的后悔与恐惧。
末了,鱼弘志环视眾人,声音中带著从未有过的无助说到:
“事情就是这样,咱家…咱家当时是昏了头,被那点权柄迷了眼。
如今是骑虎难下,仇老狗绝不会善罢甘休,诸位…都说说,眼下该如何是好?”
鱼弘志此刻方寸大乱,將希望寄託於眾人。
然而,这些心腹多是武夫或依附於他的宦官,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危局和仇士良的积威,大多面露愤慨或忧色,却无良策,只能面面相覷,最后纷纷表態:
“我等唯国公马首是瞻。”
“国公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鱼弘志看著这群人,听著他们说的话,心里更加绝望,如同坠入冰窟一样。
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一直沉默坐在角落、闭目凝思的谋士邓宇哲。
此人年约四旬,面容清癯,是鱼弘志最倚重的心腹谋士,因屡试不第投靠鱼弘志,为人机敏,善谋略。
“宇哲。”鱼弘志无奈地轻唤一声,语气带著恳求的说到:
“你怎么看?你素来足智多谋,快给咱家指条明路。”
邓宇哲闻声,缓缓睁开眼,目光清明,並无慌乱。
邓宇哲起身拱手,声音清晰而冷静的说道:
“国公勿怪,学生方才並非懈怠,实是在心中推演国公眼下的处境与破局之策。”
鱼弘志精神一振立刻说到:“快讲。”
邓宇哲捋了捋鬍鬚后沉声道:
“国公今日所为,虽稍显急切,但毕竟奉的是陛下口諭!此乃最大的护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