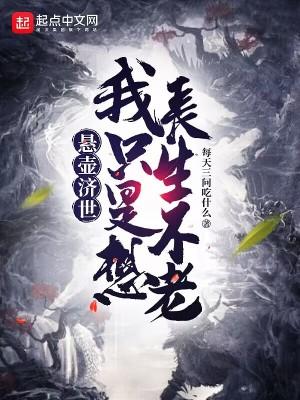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朕唐武宗开局在仇士良刀尖躺平 > 051试改科举(第2页)
051试改科举(第2页)
若贸然大幅增加取士名额,守选年限只会更长,释褐试竞爭將更残酷,最终结果要么是製造更多心怀怨望的待业士子。要么是迫使更多人流向藩镇幕府,反而助长地方势力,此乃饮鴆止渴
不能贸然扩招,官位是硬约束,財政更是枷锁。
李炎停下脚步,望著太液池微澜的水面,心中已然有了决断。
李景让可用,但培植新血之事,急不得。
“嗯,朕明白了。”李炎转过身,对陈夷行说道:
“今岁取士名额,就如此定下:
进士科,取四十人;明经科,取二百人;其余明法、明算、童子诸科,每科各取二十人。
知贡举李侍郎处,陈卿可依此传达圣意。”
“臣,领旨。”陈夷行躬身应诺。
待行至一处僻静迴廊,四下无人之时,李炎停下脚步,目光直视陈夷行,语气郑重说道:
“陈卿,朕可信你否?”
陈夷行心中一凛,环顾四周確认无耳,肃然躬身,声音压得极低却字字清晰说道:
“陛下,臣陈夷行,愿以此身家性命及世代清誉作保。
陛下今日无论所言何事,皆只出於陛下之口,入於臣之双耳。
天知地知,陛下知臣知,绝无第三人可闻。”
李炎凝视陈夷行片刻,缓缓点头说道:“好,朕信你。”
李炎负手望向远处含元殿的飞檐,声音中带著一种深沉的抱负说道:
“朕欲效太宗皇帝,揽尽天下英才,重振我大唐雄风。
前些时日国子监问政,命诸生上书言事。
虽其所言,多能切中时弊,然所提解决之道,往往失之空泛或稚嫩。”
李炎话锋一转说道:
“然朕却如获至宝,为何?盖因那一封封奏疏,字里行间,写的皆是我大唐当下实实在在的难处、痛处,此乃赤子之心,忧国之思。”
陈夷行听闻此言,眼中闪过一丝激动与欣慰——陛下果然是有为之君。
李炎接著说道:
“其中关於科举之弊,诸生所言,朕归纳数端:
一曰『行卷,考前投献诗文给权贵名流以求延誉、『公荐,官员公开推荐考生,此二者之风盛行,请託成习。
二曰考官取士,每重门第阀阅,寒素难进。
三曰进士浮华,重诗赋而轻实学。
四曰及第后『期集、『曲江宴等,易结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