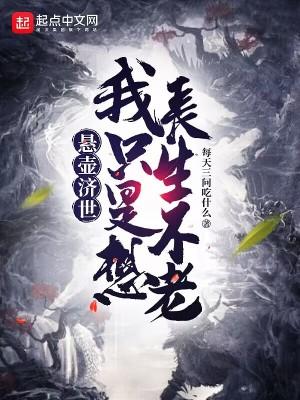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朕唐武宗开局在仇士良刀尖躺平 > 051试改科举(第3页)
051试改科举(第3页)
陈卿,此四弊,確有其事否?”
陈夷行面色凝重,坦诚以告道:
“陛下明察秋毫,此四弊,皆切中要害,確实存在。
关於行卷、公荐与考官取士重门阀,今科知贡举李景让,素以刚正、重实学、喜拔擢寒门著称。
臣料其必尽力摒除请託,唯重才学。
然门第之见,积重难返,非李侍郎一人之力可全扭。
至於进士浮华与朋党之虞,臣亦深以为然,然牵涉甚广,尚无良策禁绝。”
“朕有些想法,陈卿且听。”李炎压低声音看向陈夷行道:
“其一,为绝请託、行卷、抑门第之弊:
礼部收卷后,即刻將考生姓名、籍贯等糊封。
再遣专人文吏,用一种统一字体,將所有试卷重新誊录一遍。
誊录副本交阅卷官批阅,待定榜后,方启封原卷对照姓名。
阅卷时,设多位考官,互相监督。
此法,或可令考官但凭文章取士,不识其人门第,不知其请託何人。”
“其二,为纠进士浮华之弊:
进士科考试,可將诗赋与策论、经义分开评等。
诗赋固可显文采,然治国需实策通经。
可提高策论、经义在录取中的权重,或单设策论优异等名目。”
“其三,为防朋党:
明令禁止新科进士於守选期內,以同年之名结社、串联,尤其禁绝期集、曲江宴之外的大规模私聚,违者,严究。”
陈夷行听得眼中异彩连连,尤其对糊名、誊录二法深以为然。
陈夷行思索片刻,谨慎道:
“陛下圣虑深远,糊名、誊录之法,隔绝考官与考生之私,確为良策。
推行此法,可最大程度確保取士以才学为本。
然此乃重大变革,牵涉礼部、吏部诸多规程,恐非一蹴而就。
臣以为,可先行试点,待完善后再推及天下。”
“至於分开评等诗赋与策论经义,以及禁止及第后私聚结党,臣亦深表赞同。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