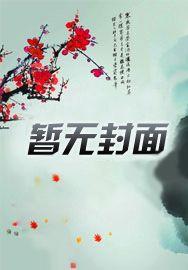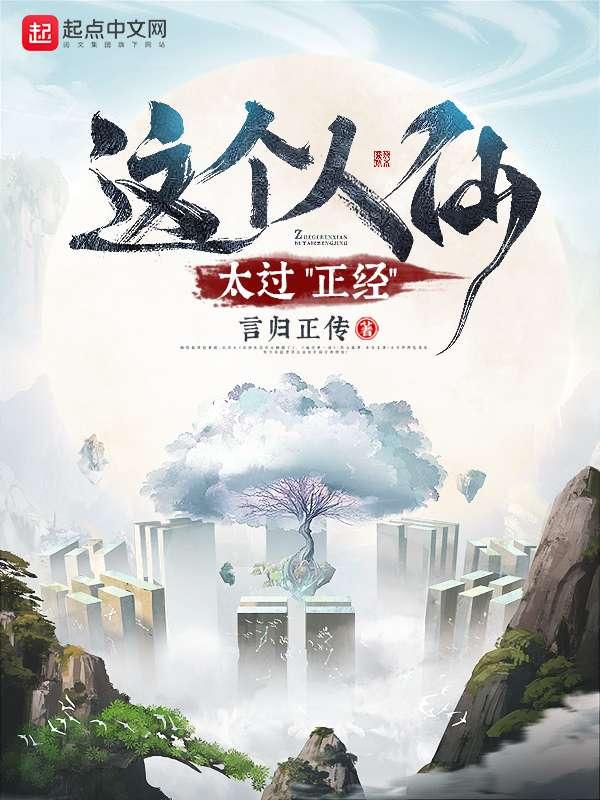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刑警日志txt电子书 > 第1917章 死者身份(第1页)
第1917章 死者身份(第1页)
小林拿着检材和报告快步走出解剖室,张凯则留在原地,对着解剖台旁的现场照片陷入沉思。照片上的帆布布袋、扳手碎片、烟蒂,与解剖发现的颈部压痕、金属碎片、搏斗痕迹,正一点点串联成线索链??虽然死者身份尚未明。。。
夜色如墨,刑侦支队的走廊里只剩几盏应急灯还亮着。杨林和杨森回到办公室,桌上堆满了勘查照片、证物清单和现场草图。两人没急着走,反而重新摊开笔记本,一帧一帧地翻看白天拍摄的照片。窗外偶尔传来警车驶过的鸣笛声,像是提醒他们时间并未停歇。
“你看这里。”杨林突然指着一张放大后的帆布碎片照片,“边缘撕裂的方向是斜向右上,说明布袋当时被树枝勾住时,是被人从左下方拖拽过去的。如果抛尸是从上游往下游走,那嫌疑人应该是逆着水流方向移动,这不符合常理。”
杨森凑近屏幕:“你是说……他不是顺着渠边走,而是从某个高处直接把尸体扔进排水口?”
“对。”杨林点头,“上游那个废弃排水口离地面有两米多高,普通人够不着,除非用了梯子或者站在车上。而且你看鞋印??43码网格纹运动鞋,在泥地上留下的压痕深度平均在1。2厘米左右,但靠近排水口那段突然变浅,只有0。6厘米。说明什么?”
“负重减轻了。”杨森接话,“他把尸体放下后才继续走的。”
两人对视一眼,几乎同时开口:“抛尸点不在下游,而在上游!下游发现的帆布碎片和烟蒂,只是运输途中掉落的残留物!”
这个推断像一道闪电劈开了迷雾。此前他们一直默认尸体是在下游被丢入水渠,因此重点排查渠岸两侧的人行路径。可现在看来,真正的抛尸入口正是那个隐蔽的废弃排水口??位置偏僻、监控死角、便于快速撤离。
“得重新调监控。”杨森立刻起身,“王帅那边应该还在查主干道的卡口,但我们要盯的是能开到上游工地附近的车辆,尤其是带货箱或后斗的小型货车、皮卡,甚至三轮摩托。”
“还有时间。”杨林看了眼电脑右下角的时间:23:。“技术科明天早上出结果,我们今晚先把路线还原出来。假设嫌疑人从某处运尸出发,途经上游排水口,再沿渠边步行一段距离以制造假象,最后从下游路口离开??这条动线必须闭环。”
他们迅速打开市域地图,标记出几个关键节点:尸体发现地(下游)、帆布碎片与烟蒂位置、废弃排水口、最近的主干道路口,以及周边三个拆迁工地的位置。其中,位于城西老工业区的“宏达机械厂旧址”最为可疑??该地块正在进行拆除作业,工人宿舍距排水渠仅800米,且围墙有一处破损长期未修。
“重点查宏达工地。”杨林圈出位置,“扳手、红砖碎屑、尼龙绳,全都能在那里找到。白色粉末如果是涂料,也可能来自隔壁正在装修的仓库。更重要的是,那里晚上没人值班,外来车辆进出不易察觉。”
正说着,手机震动。是技术科小张发来的消息:“烟蒂DNA提取失败,样本受潮严重,细胞降解。但白色粉末成分初步判定为‘外墙防水腻子’,常见于建筑外立面批刮工序;扳手碎片上的油污含有锌基抗磨剂,多用于老旧机械设备润滑;帆布缝补线材质为涤纶混棉,线径0。8毫米,属手工缝合,非工厂流水线产品。”
杨林看完,眼神一凝:“防水腻子……这种材料一般不会单独出现在工地上,它通常伴随着外墙翻新工程使用。而宏达工地主要是结构拆除,不涉及外装改造。”
“除非有人私接项目。”杨森反应过来,“比如包工头私下接了个粉刷活儿,让手下工人兼职施工。这种情况很常见,尤其是一些临时突击整改的市政工程。”
“那么问题来了。”杨林低声说,“谁既有条件接触这类材料,又能自由出入工地,还能掌握排水渠的盲区路线?”
答案呼之欲出:工地管理员、班组长,或是负责材料调度的监工。
凌晨一点十七分,陆川打来电话:“刚接到分局通报,昨晚十点左右,有居民报警称在排水渠北侧听见‘扑通’一声巨响,持续两三秒,随后一辆蓝色农用三轮车快速驶离。车型模糊,未拍清车牌,但目击者记得车尾挂着一块锈铁皮,行驶时哗啦作响。”
“农用车!”杨森猛地站起,“能载重、底盘高、不怕颠簸,完全符合运尸条件!而且这种车很少进市区,一旦出现容易引起注意,所以嫌疑人会选择夜间行动。”
“时间也吻合。”杨林快速计算,“尸体腐败程度显示死亡时间约五至七天前,抛尸应在三天内完成。昨晚十点的声响,极可能是第二次返回现场确认尸体是否冲走,或是补扔某些遗留物品。”
他们立即联系王帅调取附近治安探头。由于事发路段属于城乡结合部,监控密度低,直到调阅五个摄像头、回放四小时录像后,终于捕捉到一辆深蓝色三轮农用车的身影。车身歪斜,后斗盖着深色篷布,右后视镜缺失,车尾确实悬着一块破铁皮,随风晃动发出金属摩擦声。
“锁定这辆车。”陆川下令,“查车辆登记信息,同时派人去宏达工地摸底,重点排查近期驾驶过类似车辆的工人或管理人员。”
天刚蒙蒙亮,技术科传来新进展:帆布碎片上的白色缝补线经过显微比对,与三个月前一起工地盗窃案中遗留的安全帽内衬线材一致。当年案件未破,但现场提取到一枚手套,手套掌心处有用同种缝线修补过的痕迹。
“这是个重要关联!”杨林翻出旧案卷宗,“当年失窃的是电动切割机和一批铜缆,价值十余万。案发时间为晚间九点多,地点正是宏达工地材料库。守夜人称看到一名男子翻墙而出,身穿灰色夹克,脚穿43码运动鞋。”
“鞋码吻合。”杨森盯着照片,“而且你看这人逃跑路线??穿过厂区废料堆,跳过排水沟,直奔西北角围墙缺口。他对地形太熟了,绝对是内部人员。”
更巧的是,当年监控虽模糊,但在一处拐角拍到了嫌疑人侧影:身高约178,体型偏瘦,左手无名指戴一枚宽环戒指。而此次在烟蒂旁发现的半枚模糊掌纹边缘,经增强处理后,也显示出类似特征??掌纹走向呈典型“箕形”,且左手无名指区域有长期佩戴金属饰品造成的压痕。
“同一人作案的可能性极高。”陆川召集全体案侦人员召开晨会,“综合现有证据链:死者被帆布包裹,经农用车运至上游排水口抛入渠内;嫌疑人具备建筑行业背景,熟悉地形,抽烟习惯固定(利群),身高体重鞋码明确,并有手工缝补衣物的习惯;加之DNA虽未提取成功,但掌纹、齿痕、行动模式高度重合,我们认为,此案与三年内多起工地盗窃案存在并案侦查价值。”
会议结束,杨林带队前往宏达工地展开暗访。清晨六点半,工人们陆续进场打卡。他们在门卫处观察了半天,注意到一名叫周德海的班组长行为异常:每天最早到、最晚走,自带保温饭盒,从不参与工友聚餐;脚穿一双洗得发白的43码李宁运动鞋,鞋底花纹与现场鞋印完全匹配;更关键的是,其宿舍位于工地最角落的一间活动板房,窗户朝向正是那处废弃排水口。
“昨天他还换了新锁。”一名便衣回报,“说是怕东西被盗,其实更像是防止别人进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