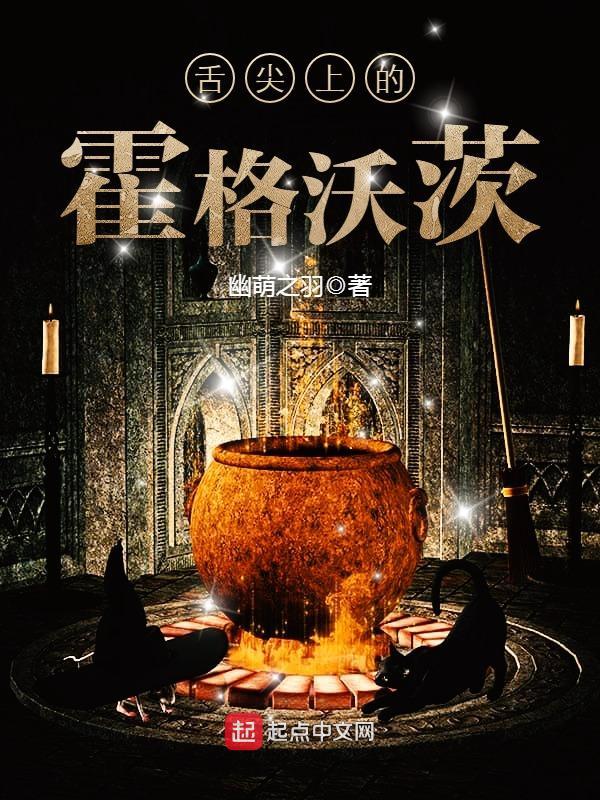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恋爱疗愈手册全文免费阅读 > 第122章 内定(第2页)
第122章 内定(第2页)
当晚,林小满在手册新页写下:
【有些话注定无法完美地说出口。
它们结巴、破碎、带着愧疚与犹豫。
但正是这些不完美的表达,
证明了一个人曾多么努力地,
试图连接另一个人的灵魂。】
陈默看完这句话,沉默许久,忽然说:“我想办一场‘声音展览’。”
“声音?”
“用录音笔收集那些不敢当面说的话。”他眼神明亮,“可以是道歉、告白、告别,或者仅仅是一句‘我今天很难受’。听众戴上耳机,走进不同的‘声音房间’,听见陌生人的真心。”
“你会担心隐私泄露吗?”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变声处理,或由他人代读。”他顿了顿,“就像你当初让我读顾言老师的信那样??有时候,借别人的声音,反而能说出最真实的话。”
他们开始筹备“耳语计划”。第一周,就收到七十三份音频投稿。其中一段录音让林小满反复听了五遍??是个男孩的声音,背景有火车轰鸣:
【爸,你在开长途货车吗?我现在在读大二,食堂的红烧肉比高中时贵了两块。上次你说“男人流血不流泪”,可我在急诊室看到你捂着手臂蹲在地上发抖……那时候我就想,你也是会疼的吧?
我不是怪你从小严格要求我。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现在过得还可以。
如果你听到这段话,请吃顿热饭,别总啃馒头。
我想你了。】
陈默将这段录音配上画面:一列夜行列车驶过旷野,车窗内映出父子模糊的轮廓,餐盒里的热气氤氲成星河。
展览开幕那夜,下起了雨。但他们没想到,仍有上百人撑伞前来。有人戴着耳机听完后久久伫立,有人悄悄把写着心事的纸条塞进展厅留言箱,还有一个中年男人,在“致逝去亲人”录音角录了整整二十分钟,出来时双眼通红,却向工作人员深深鞠了一躬。
散场时,林小满在台阶上发现一把遗落的伞。伞柄上贴着便签:【谢谢你们让我敢说出那句“妈妈,我不想你死”。】
她握着伞,站在雨中,任雨水打湿肩头。陈默跑过来,脱下外套罩在她头顶,自己淋得透湿。
“你干嘛不躲?”他喘着气笑。
“我在想,”她望着漆黑的天空,“每一个愿意说出痛苦的人,是不是都曾在某个时刻,抬头看过天,然后对自己说:再试一次?”
他握住她的手,用力捏了捏:“所以下次,我们一起抬头。”
几天后,市青少年心理协会邀请他们做经验分享。会议室里坐满了学校心理老师、社工和志愿者。林小满站在台上,投影播放着“心语墙”的成长轨迹:从最初的一片空白,到如今密密麻麻的心事森林。
“我们最初以为,要做的是‘解决问题’。”她说,“后来才发现,真正重要的是‘见证存在’。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痛苦被看见、被接纳,哪怕问题仍在,他也已经开始了治愈。”
问答环节,一位年轻教师举手:“如果……遇到像当年顾言老师那样的情况呢?就是那种,明明尽力了,学生还是走了的时刻?”
空气微微一滞。
林小满看向陈默。他微微颔首。
她深吸一口气:“我十八岁那年,差点在心理咨询室割腕。顾言老师发现了,拦住了我。但他没能阻止另一个学生??那是他带的第一个抑郁症个案,两周后跳楼了。他自责了很久,甚至一度辞职。”
台下一片寂静。
“可你知道吗?”她的声音柔和下来,“那个学生留下的日记里写着:‘顾老师是唯一一个问我“疼不疼”的大人。’就这一句话,支撑我活到了今天。”
她停顿片刻:“所以我想说,我们无法保证拯救每一个人。但我们能保证的是??当有人伸手时,我们的手就在那里。不评判,不催促,只是稳稳地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