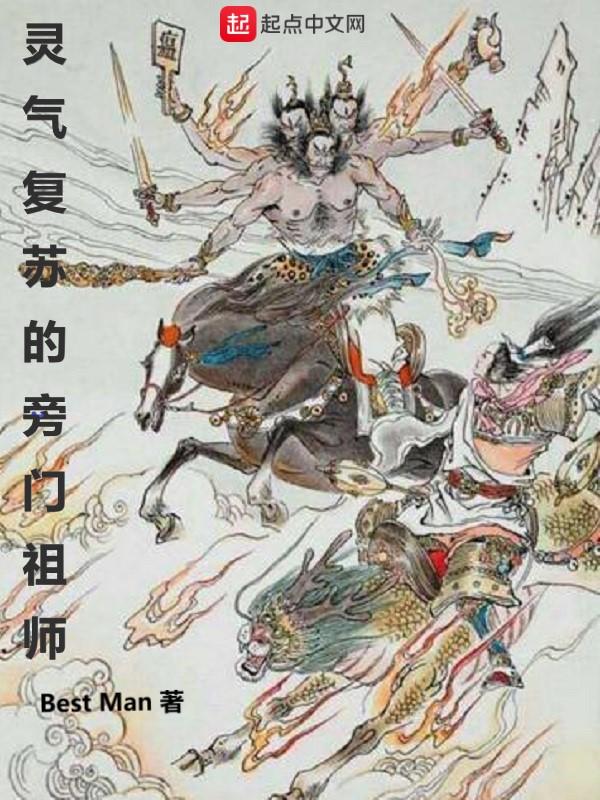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妻子浪翻了免费完整版 > 第1401章 活着真好(第2页)
第1401章 活着真好(第2页)
“到了吗?”
她走过,所以算准了我抵达邦达的时间。
“到了,邦达。”我回复,附加了一张刚刚拍下的草原日落照片。
她很快回了一个微笑的表情。
没有再多的话语,但这种跨越距离的、简单的报平安和分享,却像这高原落日的余温,熨帖着独自跋涉的孤寂。
何雅也走了出来,站在我身边,一起看着远方的落日。
“明天,”她轻声说,“就要过业拉山,去然乌湖了。”
“嗯。”我点点头,转头向她问道,“怎么样这一路走下来?”
何雅耸了耸肩道:“比想象中艰辛,不过感觉很不一样。”
“那我采访你一下,你现在是什么感觉?”
“咳咳!~”
何雅清了清嗓子,故意板起脸,用一种字正腔圆的播音腔说道:
“本台特约记者何雅,在海拔四千零八米的邦达草原为您发回现场报道。经过连日跋涉,翻越天险,此刻面对此情此景,唯一的感受就是:活着真好!”
她说完,自己先忍不住笑了起来。
眼角弯弯的,夕阳的金光落在她睫毛上,跳跃着细碎的光点。
我也被她逗笑了,配合地问道:“那么,何记者,除了‘活着真好’,这一路走来,就没有其他……更具体一点的感触吗?比如,对人,对事?”
何雅的笑容微微收敛了一些,她转过身,再次面向那一片被落日熔金浸染的草原。
她的播音腔消失了,声音恢复了平时的清亮,却多了一丝认真。
“具体的感触啊……”
她拖长了语调,像是真的在仔细思考。
半晌才说道:“感触就是,这条路上,风景是真的壮美,也是真的残酷。高反是真的难受,但身边有人递来氧气瓶和温水的时候,也是真的……温暖。”
她顿了顿,没有看我,目光依旧投向远方:“还有就是,有些人吧,平时看起来挺不靠谱的,吊儿郎当的,可真到了关键时刻,还挺靠得住的。”
她说着的同时,瞟了我一眼。
晚风吹起她额前的碎发,她抬手轻轻拢到耳后,这个细微的动作带着一种罕见的温柔。
“所以……”她终于侧过头,看向我。
眼神在夕阳的逆光中显得有些深邃,唇边带着一丝浅淡的笑意,说道:“江河,你说,我们这算不算是……患难见真情了?”
“患难见真情”这几个字,她咬得并不重,却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我心里漾开了圈圈涟漪。
这话里的含义太过模糊,可以理解为战友之间的情谊,也可以指向别的。
我看着她被霞光镀上一层柔光的侧脸,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承认吗?似乎有些逾越。
否认吗?又显得矫情和虚伪。
正当我斟酌词句时,何雅却忽然“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刚才那点微妙的气氛瞬间被她自己打破。
“瞧把你紧张的!”
她用手肘撞了我一下,恢复了平时那副爽朗的样子,“开玩笑的!咱们这当然是纯洁的革命友谊,坚不可摧!”
她笑得没心没肺,仿佛刚才那个带着试探语气说话的人不是她。
可我分明看见,在她转回头去的那一刻,眼底有一闪而过的、未被夕阳照亮的失落。
我也跟着笑了笑,顺着她的话说:“那必须的,咱们可是要一起闯羌塘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