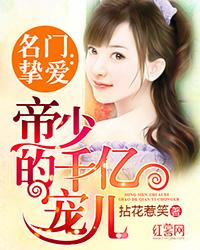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梦千年地板 > 影子(第1页)
影子(第1页)
贞观十七年四月初七,京城春意微寒。太子李治正式立储,长安宫城中却仍笼罩着一层不轻的肃穆。
一日朝堂之上,长孙无忌参奏安国夫人亦参与谋反,言辞恳切:
“臣参奏安国夫人参与此次东宫谋逆,此女怀亡国之恨,欲助太子行谋逆弑父之事以复国。”
李世民问:“无忌所言,可有证据?”
长孙无忌答:“安国夫人行事周密,因此臣目前仅有两证,一是魏征死后,安国夫人曾奉废太子私诏看望废太子,二是臣查到废太子谋事前曾有密信相通安国府。”
李世民明知故问地问道:“那密信,你可有查到,写了什么内容?”
长孙无忌说:“安国夫人已焚毁此信,臣推测必是言及谋逆之事,臣听说陛下已阅过此信,愿陛下勿被此女蒙骗,不然我大唐社稷难安矣。”
阿史那社尔此时正在朝堂之上,缓步上前,跪下:“吾姊向来心向大唐,长孙大人所言,望陛下明察。”
李世民看了看群臣,最后目光落在房玄龄身上。
房玄龄沉吟片刻,缓缓起身,拱手对李世民道:“陛下,臣以为,此事非轻言可决。安国夫人素来德行端重,若无确凿证据,贸然定罪,恐有冤枉之虞。”
长孙无忌闻言,眉头一蹙:“房卿此言虽谨慎,却恐误了社稷。女流之口,阴险莫测,陛下若不早察,社稷难保。”
李世民微微皱眉,声音沉稳而不急:“罢了,尔等皆是朕所倚重之臣,然此事,朕自有分晓。安国夫人若有异心,朕自会查明;若无,亦不可随意污之名声。”
此时,朝堂一片肃静。阿史那社尔轻轻抬头,恭敬说道:“陛下若愿,臣可为证,吾姊自无异心。”
李世民目光扫过在座群臣,缓缓说道:“既然此事关系重大,朕命房卿撤查密信之事,且查前太子近臣之行止,待真凭实据,再行定夺。”
长孙无忌面色虽有不悦,但也只能暂时忍下,恭声应道:“遵旨。”
李世民微微点头,道:“此事虽为宫廷私事,却关系大唐江山安危,尔等皆须谨言慎行。散朝。”
群臣低头行礼,纷纷退下,只余下长孙无忌与房玄龄在原位,长孙无忌低声道:“房卿,你可真替这女子说话?”
房玄龄淡然一笑:“陛下眼明心静,何须尔等多虑。只盼真相浮出水面,社稷自安。”
夜深,宫灯微亮,房玄龄步入太极殿,见李世民独自坐于龙榻之上,神色深沉。
房玄龄行礼:“陛下,房某今日到来是为早朝安国夫人一事。”
李世民抬眼,声音平静却带着几分意味:“房卿,安国夫人可否已将信重新抄录于你。”
房玄龄点头并递出一封信:“陛下,这是臣命安国夫人回忆后,她亲自抄录所得,请陛下核对。”
“夫人,魏征已逝,吾无复左膀。东宫被隔,师傅旧属皆避我如蛇蝎。父皇宠魏王愈深,群臣多以目视之,避我如尘。夫人曾言:‘慎言慎行’——承乾谨记。但我不甘。若母后在世,或许她仍能护我一线;今生无人可倚,唯夫人尚记我几分旧情。若我有一日失足,还请夫人——为我焚香一炷,不为名,只为魂归长安。”
李世民缓缓说道:“此信与原信并无字句之差。”
房玄龄微微点头,说道:“臣已细读,信中虽言‘魂归长安’,但无谋逆之意,皆为东宫孤寂之情,忧虑四方不测。”
李世民缓缓点头,眼神深沉:“卿看此信,是否可安民心?”
房玄龄低声道:“臣以为,此乃皇子孤苦之语,无关不轨。若公然追究,只恐生民疑虑,反累东宫。”
李世民叹了口气,伸手将信揉起,随意放入怀中:“房卿心意,朕自知。此事,且暂时不了了之,不必让长孙无忌等人再添风声。”
房玄龄微微一愣,随即拱手:“遵旨。”
李世民微微一笑,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卿切记,宫中之事,常需深思熟虑。言多必失,静观其变,有时胜过急于裁断。”
房玄龄顿觉陛下深意非浅,连忙低头:“臣明白,必谨守陛下意旨。”
李世民目光望向窗外夜色,声音低沉:“此后,你与无忌当同心守护东宫,不可让虚言扰乱我大唐社稷。”
房玄龄心中一凛,恭声应道:“臣誓当竭力,护东宫安宁,社稷无虞。”
夜风轻拂殿宇,宫灯摇曳,似乎连影子都在为这份深宫沉默而屏息。
因长孙无忌参奏之事,自上次召问太子人选一事后,陛下未再召我入宫,我亦听闻风声,便也远离朝堂,每日在安国府内清闲读书,偶尔去胡汉书塾看看那些学生。
二月时,李世民已令命阎立本绘二十四位功臣像于凌烟阁——西内三清殿侧。这二十四位,皆是唐初功勋卓著之臣: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直到秦叔宝。每一幅画像都神情逼真,神韵各异,皆见其一生功业与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