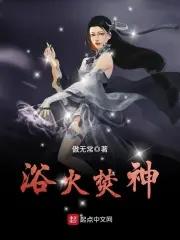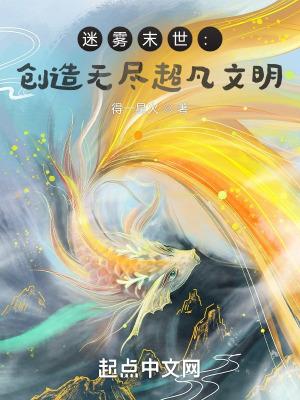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梦千年地板 > 影子(第2页)
影子(第2页)
六月盛夏时分,李世民邀我凌烟阁一见,殿内灯光柔和,画像静静排列在深红檐柱间,似在低声讲述大唐的兴衰荣辱。
李世民的目光在画像间缓缓移动,指尖轻轻划过一幅幅卷轴,低声道:“舒涵,若卿是男子……或许也能位列其中,流传后世。”
我垂首,轻声道:“陛下言重。臣不过幸得陪伴陛下左右,目睹江山之事,已是荣幸。”
李世民叹息,手指仍在画卷上停留,像是在感受每一位功臣的气息:“舒涵,你在我心中,早已超越了男女之情,非止君臣,而是……可以托付的知己。”
我抿唇,不敢与他平视,心底却明了:他信我如信自己最忠诚的臣子,也信我能看清人心、明辨是非。
我曾陪伴他雁门救驾,晋阳起兵,暗中护住大唐边境,守护后宫,维护太子,所有的秘密、委托、劝谏、疼惜,都曾属于我们之间,属于这宫殿深处的夜与光。
我轻轻低下头,手指抚过卷轴,微微一笑——这份守护,我既不求名,也无需记忆。我存在过,是他一生的影子,却不会成为历史的一笔。此时此刻也似乎读出了历史的安排:我将随他而去,最终被历史抹去。
我暗暗吐息,微微躬身:“陛下,无需多言。功名、史册,皆非我之所求。只愿您安好,黎民康宁。”
他没有开口,只是久久凝视。我能感受到那份无声的理解——他明白,而我也明白,这份默默无言的守护,将永远属于他,却不属于任何人。
夜色深沉,宫灯摇曳。我站在凌烟阁中,看着那些永世流传的名字,心底却清楚:自己的名字,将随着他的离去,从历史里悄然消失。
同月,李世民欲亲征高句丽,诏我入宫问策。自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出嫁后,我已经有两年多未与他同席而坐。
李世民缓缓开口:“今日诏卿前来,是为远征一事,卿聪慧过人,可知此役成败?”
我低声而坚定地说:“陛下,京师虽安,但高句丽国土辽远,秋冬交替,军旅劳顿,陛下身躯尚未康健,恐有不便。”
他轻轻摇头,眼底却闪过一丝柔和的光:“卿担心朕身体,朕自知。然边疆之事,不可拖延,国事重于身躯。”
我垂下眼,知道此刻再多言,只会显得无力。我伴他许多年,劝谏、辅佐、守护,他听我言时多有采纳,可今次——历史的车轮已不可逆转。
我明白他的心意——那份征服边疆的决心、保卫社稷的热忱,比任何安危都更重要。他眉目间的坚毅,让人无法轻易劝阻。
可我更清楚,那一次征伐之后,他的身躯将渐渐不如从前,而我的命运,也将随他一同被历史悄然抹去。
我心中微动,却依旧面无波澜,淡声说道:“臣请随陛下征战,愿陛下同意臣之所请。”
李世民目光凝视我,沉默良久。烛光映在他的面庞,映出一抹难得的柔和。
“舒涵……”他低声唤我的名字,语气里既有玩笑,又带着些许无奈,“朕知道你心意坚定。”
他顿了顿,手指轻敲案几,“既然你执意,我自不能阻你随军。只是……你须在军中以正役从之,随朕巡阵,切勿轻举妄动,以免扰乱军心。”
我心中一暖,低声应:“臣谨遵陛下旨意,绝不妄为。”
他轻轻点头,目光又深又远:“好……朕放心你在侧。战场险恶,但有你陪在身旁,朕亦增一分胆气。”
贞观十七年七月,晨光微凉,时隔多年,我再次女扮男装,私下顶替了一位陛下亲兵。我随御驾出城,沿着长安城外的青石大道,心中百感交集。
皇帝策马在前,披着战袍,神色凝重而坚毅。黎明前的天色灰白,营帐间静得出奇。寒风吹过,我紧裹衣衫,却依然感到一阵刺骨。李世民早已整装待发,骑在战马上,目光如鹰般锐利。火光映在铠甲上,他的面容比平日更显刚毅。
我悄悄跟随在侧,不敢发出半点声响。每一次他挥剑,指挥军阵,我都能感受到那份历经沙场磨炼的沉稳与果断。他低声呼唤:“舒涵,看这里,敌军若从此道入,我军应分两翼布防。”
我俯身在帐中摆好沙盘,亦轻声道:“陛下若照此布置,敌军必受困,我军可一举夺阵。”
他抬眼看我,眉梢闪过一抹笑意。“你在后方等着,朕一定给你带回好消息。”
我低头微笑,心底却清楚,这不是玩笑——每一场布阵,每一次攻防,都关系到无数将士的生死。
战鼓声起,旌旗猎猎。夜色与烟尘混杂,箭矢呼啸而过,战马嘶鸣。李世民在前方指挥,每一步都精准而迅速,而我则暗中关注营帐布置、补给路线以及后方安危,确保他无虞。
一次突袭间,李世民身边的旗帜被风吹倒,我几乎是瞬间奔出,将一名随军小将拦下,并扶稳旗杆。他侧目看我,眼底闪过一丝欣慰:“你总是比朕先想到细节,真是朕的影子啊。”
我心头一震,却只是低声答:“陛下平安,臣便安心。”
夜色沉沉,营帐内外,战事尚未平息。我倚在帐幔旁,看着他疲惫却目光坚定的侧脸。火光摇曳,将他的影子映在帷帐上,如同一位永不退缩的帝王,而我,如同他身后的影子,默默守护。
每一夜,我都替他整理军情册册,将敌情、军力、兵员尽数记下。我知道,这些事情或许无人得见,历史不会为我记下半字一言,但我心安——因为我护佑了他,护佑了大唐。
九月,唐攻安市不能克,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