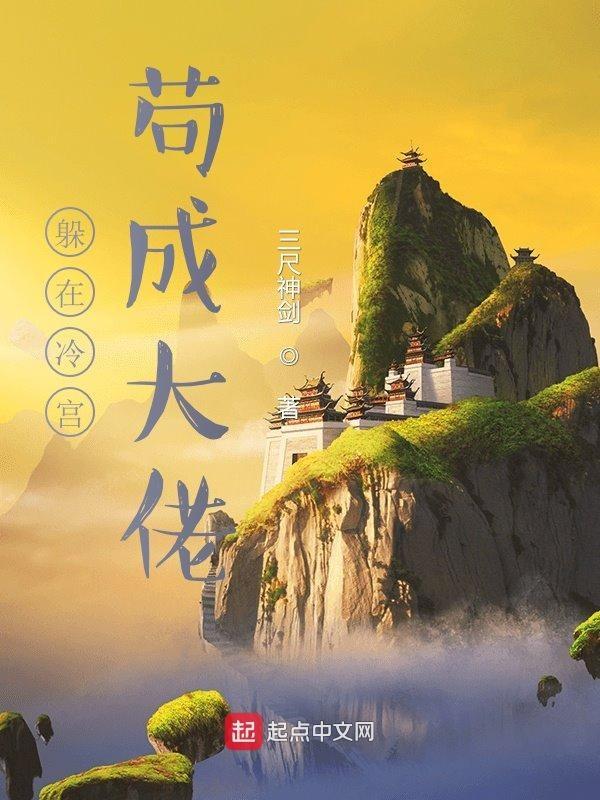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梦千年板材 > 暗涌(第2页)
暗涌(第2页)
“陛下明察万机,却未察己心。您的喜怒,天下皆察;您的偏爱,太子更察。”
他一怔,似被触动。
“我知他叛逆,却仍忍不住想试着磨他。”李世民苦笑一声,“若非今日他们在朝堂上明言争论,朕一直以为他们还同之前一样互敬互爱。”
我缓缓走近,声音轻柔而沉静:
“陛下对太子严,对魏王宽并非刻意为之,严厉与慈爱皆为父恩,然太子恨父,魏王生娇,若陛下问天下人,他们只会记得陛下偏心魏王,甚至暗自揣度陛下是不是欲废太子而立魏王。”
他久久无言,目光移向窗外的风景。
“此话也就只有你敢明言于朕了。”
“因为我不在局中。”我答,“陛下是高高在上的帝王,又身处其中,今日臣斗胆明言,只是希望陛下可以早做抉择,若欲维护太子,从此应当疏远魏王,若陛下欲废承乾之位当早做安排。”
“太子是嫡长,立之十余年。若今废之,不仅宗庙震动,群臣生疑,天下必议朕反复无常。可若不废,他心性若此,又如何继大统?”
他的手指轻叩窗沿,每一次叩击都像是在衡量利与害。
“魏王……泰儿聪慧,但过于心计。朕喜其才,却厌其志。然偏他事事周全、言辞恭谨,与承乾那股少年意气相比……唉。”
他叹了一口气,像是在自嘲:“也许朕真是个糊涂的父亲。”
我低声道:“陛下不是糊涂,而是太明白。太明白,反倒更难决断。”
他回过头,注视我。那一刻,他眼底的疲惫几乎掩不住——
那不是帝王的神色,而是一个被责任与情感撕扯的父亲。
“你说得对。”他终于低语,“此事,不可再迟。太子与魏王,朕都不能再纵。”
我抬首望他,他神色渐渐收敛,眼中重新燃起一丝冷意。
那是帝王的目光,沉稳而决绝。
沉默片刻,他缓缓开口,声音低而带着好奇:“你素来淡泊名利,为何这次愿意牵扯进如此重大的朝堂之事?莫非……也是皇后之托?”
我微垂首,轻声而坚定:“陛下,此事非皇后所托,亦非为名利而言,只因……知此事若迟疑,兄弟间必生嫌隙,后果或牵连无数。臣虽身居外位,但心念天下安危,不敢袖手旁观。”
李世民轻轻点头,眉间柔和了些,眼底闪过一丝复杂的笑意:“朕明白。你心思深沉,未必为当世,但为天下计,比朕许多大臣更清楚。”
我微微行礼,心中暗自感慨:能在这历史的十字路口为他分忧,即便不能改变终局,也算尽了自己的一份心力。
那日后,李世民再未赏赐李泰逾越的宫院和金银,并疏远了魏王,太子与魏王之争渐趋和缓。然而我知道这些仍不能阻止结局。
九月初,李世民以魏征为太子少师,以稳承乾之位。承乾也确实收敛了许多,未再行狂悖之事。消息传至安国府,我静坐案前,手指轻抚着尚未批阅完的文书,心中微微叹息——这一步看似稳妥,却也暗藏隐患。
我心中微痛,知道历史终归还是要按既定的轨迹发展,
贞观十六年冬日,我接到诏书——陛下召见我入宫。
甘露殿内,李世民神色凝重,目光掠向案上的奏折:“魏征已立少师,承乾也已自省,魏王亦当有所制。”
我垂首行礼,轻声道:“陛下所虑未尝不有。太子历来自尊心强,遇此布置,心中或仍难平。魏王虽聪慧,却未必懂得自持。”
片刻,他低声道:“你前岁所言,朕未忘。你劝朕若不废太子,应该疏远魏王……但他终究聪慧,又无过错,朕亦不忍心让他离京。”
我知他言外之意。
“难舍”的并非亲情,而是李泰那种“让他看到大唐学问、版图、文治未来”的影子。那是李世民理想的折射——一个“学识与天下兼备”的子嗣。
我深吸一口气,语气极轻:“陛下可曾想过,魏王之才若不疏,终将反噬。”
他抬头,眉间一沉。
“反噬?”
我跪下,额头贴地:“陛下,魏王才华固然卓绝,但天下臣民皆言‘陛下偏魏王、轻太子’。臣斗胆相劝,可赐魏王外镇,以功名磨心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