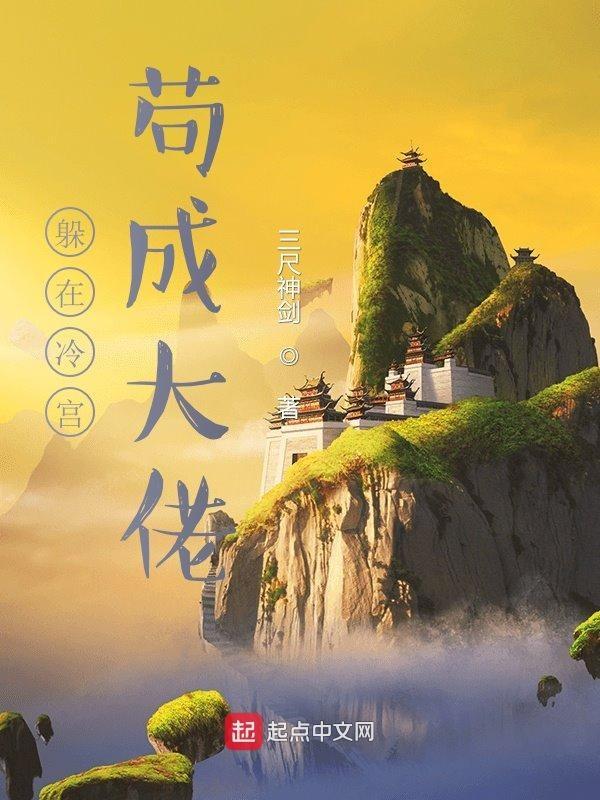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帝御山河 > 第十九回 献美惊破知己梦 卸裙难测侯爷心(第2页)
第十九回 献美惊破知己梦 卸裙难测侯爷心(第2页)
张翠喜望着案上跳动的烛火,轻轻叹了一声,声音里裹着化不开的怅然:“像我这般出身的女子,命如飘萍,在水里打了六年转,早没了扎根的力气,也只能浪荡于人世间。人生虽多歧路,可侯爷指的那些路,都是给清白人家姑娘走的,我……恐怕要等我下一世投个好胎,才能走得成。”她说着,手掌攥了攥裙摆,垂眸时眼睫上还沾着未干的湿意,满是神伤——她不是没想过,只是“乐籍出身”四个字,像块烙印,让她不敢想。
王世烈闻言,眉头微蹙,却没急着接话,半晌才缓缓开口:“姑娘莫要妄自菲薄。我倒听说,你有位知己,名唤李云舒?是个会写曲的读书人,此人对你,似是颇有些心意,没嫌过你的出身吧?”
“侯爷切莫胡乱猜想!”张翠喜猛地抬头,脸颊泛起薄红,语气里带着几分急嗔,“我与李公子不过是知音好友,论曲谈词罢了,从没想过旁的。况且他是清白人家的公子,前途正好,要考科举做大事的,我这般过往,岂不是要耽误了他?我不能害了他。”
王世烈看着她眼底的慌乱与自轻,轻轻摇了摇头,起身从桌边端过一盏热茶,缓步递到她面前,语气里满是恳切:“姑娘,我王某虽出身贵戚,却也知‘人不可貌相,命不可轻判’的道理。你既有清透的嗓子,又有懂曲的慧心,何必因过往困住自己?这杯茶你先暖暖手,莫要把自己看得太低——你的路,未必就只能是从前那样,也未必会耽误谁。”
张翠喜刚要起身道谢,却被王世烈抬手轻轻止住。他眼神温和,语气比方才更柔了几分:“姑娘不必多言,你心中所想,我大抵都明白——怕被人嫌弃,怕再被当作物件转手,怕给旁人添麻烦。”
他重新坐回椅上,目光落在她攥着茶杯的手——指节因用力而泛白,杯沿还沾着几点未干的泪痕。“我知你这些年在乐班,看惯了人情冷暖,也怕极了再被人当作物件转手,所以才不敢信旁人,不敢想未来。”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似在同她轻声絮语,“从前你身不由己,在那朱楼里唱曲,是命;可如今你赎了身,若还把自己困在‘只能卖唱’‘只能配卑贱人家’的念头里,便是自己拘着自己了。”
这话没提半个“贱籍”,却让张翠喜鼻尖一酸——她何尝不想寻条别的路,可“乐籍出身”四个字,早像烙印般刻在身上,旁人看她的眼神,总带着几分轻慢,连她自己都快信了“自己只配卑贱”。
王世烈似看穿了她的心思,继续说道:“我对姑娘,确实有倾慕之意,不然也不会因你的曲子记挂至今,更不会管这闲事。可我王某虽在京中待惯了,却也知‘强扭的瓜不甜’,更不会做那逼良为娼的事,让你受委屈。”他抬手拂去袖口的一点炭灰,语气里满是恳切,“我只盼你明白,你如今是自由身,不是那戏文里任人摆布的‘商女’。若你想寻个清静地方过日子,我能为你寻处带院子的宅院,让你种些海棠;若你还想唱曲,也不必再去暖乐楼那般地方看人脸色——你的嗓子,该配更干净的听客,也该配你自己想要的日子,而不是被我或是谁绑着。”
张翠喜握着茶杯的手渐渐松了,温热的茶汤透过瓷壁传到掌心,竟让她眼眶又热了几分。她抬头望他,见他眼神清明,没有半分轻薄,倒有几分真心实意的疼惜,心里那道因“出身”筑起的墙,竟悄悄塌了一角——原来真的有人,没嫌她的出身,还劝她为自己活。
张翠喜闻言,握着茶杯的手轻轻顿了顿,终是没接话,只低低“嗯”了一声,声音里带着点不易察觉的哽咽。王世烈见她神色稍缓,嘴角微微上扬,起身往门口走:“姑娘,如今天色已晚,你早些休息,养足了精神,明日再慢慢想往后的路,想好了再告诉我也不迟。”说罢便轻轻带上门,脚步声渐远,没再打扰她。
那一夜,厢房里的烛火燃到过半,张翠喜还坐在桌边。她望着窗外的月影,手里攥着那支旧银簪,脑子里反复转着王世烈的话——一会儿是“自由身不必困于旧路”,一会儿是“怕再被当作物件转手”,一会儿又是李云舒的笑脸,翻来覆去直到天快亮,才靠着椅背眯了片刻,眼底满是红血丝。
与此同时,暖乐楼的大堂还亮着两盏风灯。李云舒攥着刚誊好的曲谱,纸上是他熬夜改的“秋棠引”,脚步匆匆踏进来,扫了圈空荡荡的大堂,心里咯噔一下,急忙拉住个正收拾茶具的小厮:“哎!张姑娘呢?我约了她今日论新曲,怎么没见人?她往日这个时辰早来了!”
小厮直起腰,擦了擦手里的茶盏,语气里带着点唏嘘:“李公子您还不知道啊?张姑娘被杜太守赎身了,下午就被人接走了,说是去了太守府。”
“赎身?”李云舒手里的曲谱“哗啦”掉在地上,纸张散了一地,他慌忙蹲下去捡,手指都在抖,声音都发颤:“谁、谁赎的她?杜太守为什么要赎她?她……她愿意吗?”
“还能为什么?”小厮压低声音,凑到他耳边,语气里带着点暧昧的揣测,“咱楼里人都猜,是要把张姑娘献给桂宁侯当礼物呢!听说花了三万两白银,堆得跟小山似的——李公子,您往后怕是难再跟张姑娘论曲了。”
“不可能!”李云舒猛地后退一步,身子晃了晃,差点撞翻身后的八仙椅。他攥着捡起来的曲谱,指节捏得发白,眼里满是慌乱与不信,“翠喜姑娘绝不会愿意的!她不是那种贪图富贵的人,更不会甘心做别人的‘礼物’!”
说罢,他转身就往外跑,连掉在地上的折扇都忘了捡,一路跌跌撞撞往张翠喜的私家别院奔去。夜风吹得他脸颊发疼,小厮的话却在耳边反复回响,每一句都像刀子似的扎在心上——三万两、献给侯爷、礼物……这些词让他浑身发冷,只盼着能到别院见上张翠喜一面,听她亲口说一句“不是这样的”。
可到了院门口,只见朱门紧闭,门环上还挂着把铜锁,锁上已经积了层薄灰。院里的秋海棠落了满地,花瓣被夜风卷着贴在门上,透着股萧瑟的冷清。李云舒扶着门框,愣愣地站着,指尖触到冰凉的木门时,才猛地反应过来——她真的走了,被杜太守接走了,或许真的要被献给桂宁侯了。
他张了张嘴,想喊一声“翠喜姑娘”,却发不出半点声音,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门阶的青石板上,晕开一小片湿痕。直到天快亮时,他才踉跄着离开,走到街头看见几个乞丐蹲在墙角,忽然停下脚步——他从怀里掏出仅剩的碎银,又找纸笔写下一首童谣,塞给乞丐:“帮我把这个唱遍城阳郡,这些银子都是你们的。”
当日午后,城阳的街头巷尾就响起了乞丐的传唱声:“城阳郡里有桩奇,白银堆成小山齐。一只雀儿往南飞,落在侯爷暖阁西。田埂草枯盼雨露,暖阁笙歌日头低——”歌声飘进太守府的院墙时,张翠喜刚用完午饭,正坐在窗边发呆,听见这童谣,手指猛地一顿——这词里的“雀儿”“暖阁”,分明说的是自己,而这曲风,她再熟悉不过,是李云舒的手笔。
她望着窗外的天空,眼眶又热了,心里却比昨夜更乱——李云舒定是误会了,可她如今被困在太守府,连出门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正恍惚间,侍女进来回话:“姑娘,桂宁侯来了。”
张翠喜猛地回神,连忙起身整理裙摆。她望着镜中自己素净的脸庞,忽然咬了咬唇——昨夜王世烈的话还在耳边,今日李云舒的童谣又让她心焦,或许……或许主动些,才能寻条出路。她唤来侍女:“备水,我要沐浴更衣,再取妆奁来——螺子黛、胭脂膏、那支赤金点翠步摇,都拿来。”
侍女虽疑惑,却还是照办了。热水里撒了白梅瓣,氤氲的雾气漫上脸颊,张翠喜望着水面上自己的倒影,深吸了口气——她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任人摆布,哪怕这条路是自己选的,也要走得明白。
沐浴过后,侍女为她挽了垂云髻,鬓边簪上赤金点翠步摇,又用螺子黛细细勾勒眉峰,蔷薇色的胭脂轻点双颊,唇上敷了两层口脂。镜中的女子褪去了往日的清愁,添了几分明艳,连眼神都多了些决绝。张翠喜望着镜中的自己,轻声道:“去请桂宁侯来我这厢房。”
小厮得了吩咐,一路跑到驿馆,见了王世烈便躬身回话:“侯爷,张姑娘遣小的来请您,说有要事相见。”
王世烈正把玩着核桃,闻言眼底闪过丝讶异——这姑娘昨日还满是戒备,今日竟主动相邀?他放下核桃,起身道:“备轿。”
到了张翠喜的厢房外,王世烈推门进去,便见她立在烛火旁,藕粉纱裙衬得身姿窈窕,鬓边的步摇随呼吸轻晃,珍珠碎光落在她脸上,竟比满室烛火更显动人。他心中微动,面上却依旧平静,颔首道:“姑娘深夜相邀,不知有何事?”
张翠喜望着他,手指攥了攥裙摆,终是开口,声音带着几分破釜沉舟的坚定:“侯爷,我张翠喜此生,大抵也只能跟着侯爷您了。您若不嫌弃我曾是乐籍伶人,我便愿侍奉左右,绝无半句怨言。”
说罢,她便要屈膝下跪,却被王世烈快步上前扶住。他握着她的胳膊,指腹触到她微凉的肌肤,语气坦然:“姑娘快起!伶人又如何?你凭琵琶唱曲讨生活,比那些靠钻营求官的人干净多了,何必自轻至此?”
他扶着张翠喜在床沿坐下,自己则走到桌边落座,指尖无意识摩挲着杯沿——他倒想看看,这姑娘今日这般盛装相邀,究竟是何用意。
谁知张翠喜坐稳后,竟抬手去解裙上的系带。藕粉纱裙顺着肩头滑落,露出内里杏色肚兜,肌肤在烛火下泛着莹润的光,连颈间的碎发都透着几分魅惑。她抬眼望王世烈,眼神里带着几分期待,又有几分不安:“侯爷……”
王世烈看在眼里,神色却依旧平静,没有半分惊艳或轻薄,只缓缓开口,语气带着几分温和的疏离:“穿上吧。夜里天凉,仔细冻着身子。”
张翠喜的动作猛地顿住,不解地望着他——她都已做到这份上,为何他还是这般态度?是嫌弃自己的出身,还是嫌自己不是完璧之身?她嘴唇动了动,想说些什么,却见王世烈起身,走到门口又停下,回头看她:“你若只是想寻个安身之处,明日我便让人给你寻处宅院,离城不远,有个小院子,能种你喜欢的海棠。至于‘侍奉’,不必了——我要的不是一个被迫低头的人,你该为自己活。”
话音落,房门轻轻合上,只留下张翠喜愣坐在床沿,身上还披着半褪的纱裙,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填得满满当当,又空落落的——她以为自己主动献祭就能换来安稳,却没料到,王世烈给她的,是她从未敢想的“为自己活”的机会。窗外的童谣还在隐约传唱,她望着桌上那支旧银簪,忽然笑了,眼泪却顺着脸颊滑了下来——原来这世上,真的有人,不会把她当物件,只会把她当“张翠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