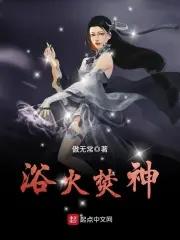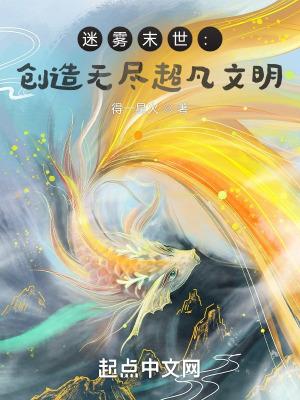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血色迷情种丹妮 > 迷雾深重1(第1页)
迷雾深重1(第1页)
边镇的寒风,似挟着塞外万年不化的冰屑,呼啸着穿透一切屏障,直往人的骨缝里钻。它将京城的脂粉香气与那些盘根错节的阴谋算计,都远远冻结在了身后,留在这片天地间的,唯有最原始、最凛冽的生存法则。
蓟镇之事沈从砚很迅速就解决了,留着几个手下善后,尘埃差不多落定,卷宗封存,但沈从砚却并未如常例立即返京复命。他手持勘合,以督查九边备御为由,带着林以墨与少数亲信,继续向着东北方向,朝着那座如同巨兽般匍匐在帝国咽喉上的坚城,辽东督师驻地宁远城而去。
路途越往北,景象越发显得肃杀而苍凉。广袤无垠的原野被一层厚厚的、仿佛永不解冻的积雪覆盖,天地间只剩下黑白二色,单调得令人心头发紧。村落稀疏得如同秃子头上的毛发,残破的土墙在风雪中瑟瑟发抖,偶尔可见大片被焚毁的废墟,焦黑的木料与断壁残垣无声地诉说着曾经的劫难,尖锐地提醒着每一个过客,此地离血肉横飞的前线并不遥远。
冻得硬邦邦的道路上,往来最多的,是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运粮民夫,他们拖着沉重的步伐,在皮鞭的呼哨声中艰难前行;以及那些神情疲惫、甲胄破旧甚至带着刀箭伤痕的巡哨士卒,他们的眼神如同这天气一般冰冷,警惕地扫视着茫茫雪原。
林以墨坐在不断颠簸的马车里,厚厚的棉帘也挡不住那无孔不入的寒气。她望着窗外飞速掠过的荒凉景象,心中那份因蓟镇雪夜与沈从砚短暂谈心而泛起的、若有若无的微澜,此刻已被眼前这赤裸而沉重的现实感彻底取代。
寒意顺着脚底蔓延至全身。这就是父亲那些密密麻麻的笔记中反复提到的、需要巨额饷银才能勉强支撑的辽东防线?这就是沈从砚口中,为了维持某种岌岌可危的平衡,甚至不惜掩盖部分血淋淋真相来竭力保全的大局?字里行间的数字,此刻化作了眼前具象的苦难与疮痍,压得她几乎喘不过气。
数日后,在一片铅灰色的天幕下,宁远城那巍峨而饱经战火的城墙,终于如同沉睡的巨兽,出现在地平线上。城头之上,无数面旌旗在强劲的北风中猎猎作响,旗面破损,颜色褪却,却依旧顽强地舞动,透着一股浸入骨髓的悲壮与坚毅。
入城的过程简单而迅捷,带着一种战时的紧张与效率。沈从砚并未多做停留,带着以轻装简行身着奴仆衣着的林以墨径直前往那座象征着辽东最高权力中枢的督师府,拜会那位名震天下的辽东督师袁崇焕。
督师府内,与外间的酷寒截然不同,上好的银炭在巨大的铜盆中烧得正旺,噼啪作响,驱散着北地那种深入骨髓的寒意。袁崇焕并未身着象征一品大员的绯色官袍,只是一身半旧的青布直裰,洗得有些发白。他面容清癯,颧骨微凸,一双眼睛却锐利得如同翱翔于雪原之上的鹰隼,目光扫过时,带着久经沙场淬炼出的风霜与一种不容置疑、近乎霸道的威严。
“沈指挥使远道而来,辛苦了。”袁崇焕的声音洪亮,中气十足,透着武人特有的干脆利落,没有丝毫文官的迂回寒暄。他对沈从砚的态度不算热络,却也保持着官场上基本的礼节。显然,他对朝廷派来的锦衣卫,尤其是眼前这位名声在外、能止小儿夜啼的“沈阎王”,抱有十二分的警惕与审视。
“袁督师坐镇危疆,御虏守土,才是真辛苦。”沈从砚拱手,语气平淡得听不出丝毫情绪,如同他此刻毫无波澜的脸,“本官奉旨巡查边备,蓟镇之事已毕,特来辽东,一是仰慕督师威仪,二来,也是想亲眼看看前线真实情形,回京后方能向陛下如实禀奏,不负圣恩。”
袁崇焕闻言,脸上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讥诮,嘴角微微向下弯了弯:“如实禀奏?呵。”他短促地笑了一声,那笑声里却毫无暖意,“朝廷若真愿听实话,看得见辽东将士的浴血,我麾下这十万儿郎,又何至于时常为区区粮饷军械发愁,乃至饥寒交迫!”他目光如电,骤然射向沈从砚,仿佛要穿透他那张波澜不惊的面具,“沈指挥使久在京城,身处枢机之地,想必比本督更清楚,每年户部拨付辽东的这数百万两饷银,漂没之后,能有多少真正落到一线将士手中?能换来多少实实在在的粮草、多少副御寒的棉甲、多少门堪用的火器?”
他不等沈从砚回答,或许也根本不需要回答,便继续道,声音愈发沉凝:“建奴努尔哈赤父子,狼子野心,虎视眈眈,宁远、锦州一线,全赖将士用命,方得数次保全。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军中缺饷已近三月,士卒饥寒,怨声渐起。长此以往,军心不稳,恐生肘腋之变!沈指挥使回京后,若能据实奏明此间困境,催请粮饷速发,便是我辽东军民之幸,亦是朝廷之福!”话语掷地有声,每一个字都带着沉甸甸的分量和一丝被强行压抑住的悲愤。
沈从砚沉默地听着,面上依旧不动声色,仿佛一尊冰雕,心中却是一沉,如同坠入了宁远城外的冰海。袁崇焕所言,与他沿途所见及暗中了解的情况相互印证,分毫不差。辽东局势,远比京城官场传闻的更为严峻,更为脆弱。这已不仅仅是贪墨腐败的问题,而是关乎整条防线存亡、国本是否动摇的致命危机。
“督师之言,字字恳切,本官记下了。”沈从砚沉声道,声音在温暖的厅堂里显得格外清晰,“粮饷之事,关乎国本,关乎社稷安危,朝廷必有考量,陛下亦会圣裁。”他话锋微转,似是无意间提及,目光却若有实质地落在袁崇焕脸上,“只是。。。近来京城查处一桩旧案,涉及通州北仓巨额亏空,其中些许线索,盘根错节,似乎隐约与辽东某些旧日往来有关,不知督师坐镇此地,可曾听闻过什么风声?”
他问得模糊而谨慎,像是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试探着水下的动静。
袁崇焕眉头微皱,沉吟片刻,摇了摇头,脸上是纯粹的不解与漠然:“边镇与京城,相隔何止千里,消息闭塞,军书旁午。本督只知日夜练兵备战,筹措粮饷已是焦头烂额,实在无暇也无力顾及京城旧案。”他顿了顿,意味深长地看了沈从砚一眼,那目光中带着告诫,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沈指挥使,辽东之事,千头万绪,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些事,追查过甚,深究到底,恐非朝廷之福,亦非边关之幸,望大人慎之。”
这话,已是近乎直白的警告。他在暗示沈从砚,若在辽东这片本就敏感脆弱的土地上,深究北仓案的线索,很可能会引爆不可控的后果,甚至动摇这用无数血肉勉强维持住的、脆弱的边防平衡。
沈从砚心中了然。袁崇焕未必清楚北仓案的具体内情,但他凭借封疆大吏的本能,敏锐地察觉到,任何来自京城的、不受控制的深入调查,都可能成为打破辽东目前危险平衡的那根稻草。
就在这时,一名亲兵步履匆匆入内,带着一身寒气,在袁崇焕耳边低语几句。袁崇焕面色一凝,瞬间恢复了那位杀伐决断的军事统帅气质,对沈从砚略一拱手:“沈指挥使,军情紧急,建奴游骑似有异动,本督失陪了。你在宁远期间,可凭勘合自行查看防务、仓储,但请谨记,莫要干扰正常军务,一切以守土安民为重。”
送走雷厉风行的袁崇焕,沈从砚独自站在督师府前冰冷的石阶上,寒意瞬间包裹了他。他望着远处校场上正在冒着严寒操练的士兵们,他们呵出的团团白气连成一片,号子声在冷风中传得老远,眼神愈发深邃难测。
林以墨一直安静地如同影子般跟在沈从砚身后,此时才敢轻轻上前半步,低声道:“袁督师他。。。似乎很不愿,甚至有些忌讳我们在此地深查下去。”
“他不是不愿,是不能,亦是不敢。”沈从砚的声音低沉,仿佛在与这凛冽的空气对话,“他需要稳定,需要朝廷持续的、哪怕是被层层克扣后的饷银,来维持这条防线不至于崩溃。任何可能引发朝堂震荡、导致前线断饷的调查,都是他绝不能容忍的变数。”
他转过头,看向林以墨,风雪似乎在他那双墨色的眸子里凝聚成了漩涡:“但我们必须要查下去。北仓案的根,或许并不在京城那些蠹虫身上,而就在这里,在这片被血与火反复浸染的土地上。你父亲笔记中那语焉不详的北风,指向的,恐怕不仅仅是关外的建奴。。。”
他的目光越过宁远城高耸的箭楼,投向更北方,那片被无尽冰雪和战争阴云笼罩的、广袤而神秘的土地。
那里,似乎隐藏着比蓟镇更深的谜团,更庞大的阴影,以及。。。更加致命的危险。
风声像战鼓,也像命运在催债。
宁远城的气氛,在袁崇焕接见之后,并未缓和,反而如同一张被拉到极致的弓弦,愈发紧绷,仿佛一点火星就能引发惊天爆炸。
袁崇焕那混合着警告与无奈的言辞犹在耳畔,沈从砚明面上的巡查也变得更为谨慎,几乎可称是走马观花。但他并未真正停止调查,只是将行动转入更深的暗处,如同潜行的猎豹。凭借锦衣卫指挥使的权限,他以核查军备仓储、评估防务效能为名,调阅了近几年来辽东部分军需物资,尤其是粮草与饷银的入库记录、分配文书及核销账目。
林以墨则彻底埋首于故纸堆中,利用其与生俱来的、对数字和细节异常缜密的特长,夜以继日地协助沈从砚在浩如烟海、字迹潦草的文牍中,艰难地梳理、比对,寻找任何可能与北仓案亏空,或是与父亲笔记中那些奇特暗记相关的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