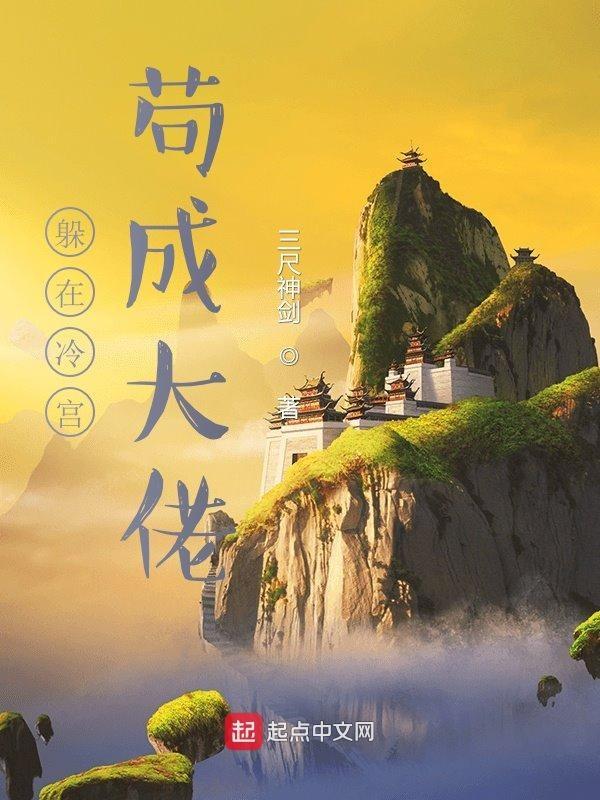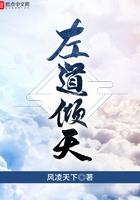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三国从樵夫到季汉上将军 > 第151章 牛憨 这个妹妹我好像认得(第2页)
第151章 牛憨 这个妹妹我好像认得(第2页)
刘璋闻言愕然,心中不安骤起。他环顾左右,发现城中兵马皆换新装,旗帜鲜明,纪律森严,分明已是敌军入驻。欲返成都,道路已被封锁;欲强闯,身边仅三千疲兵,不堪一战。
当夜,刘璋辗转难眠。忽有内侍密报:张松已被捕下狱,罪名“勾结外臣,图谋废立”。刘璋惊骇万分,始知自己落入圈套。
十八日,诸葛亮悄然入城,登门拜见。他未着官服,仅披鹤氅,执羽扇,温言道:“主公仁厚,不忍加兵于州牧,故遣亮前来劝谕。今曹操虎视关中,孙权觊觎江南,益州危如累卵。唯有托付贤主,方可保全社稷。将军若能顺应天命,禅位于皇叔刘备,非但可保富贵终身,更能青史留名,为汉室忠臣。”
刘璋泪流满面:“我非不愿让位,实恐天下讥我无能亡国啊!”
诸葛亮叹曰:“昔尧舜禅让,传为美谈。能识天命,让贤于能,正是圣君之举。若死守虚名,致百姓涂炭,才是真正的不忠不仁。”
刘璋沉默良久,终点头应允。
二十日,校尉突然现身江州,率军列阵城外,甲光耀日。他并未进城,只是派人送来一封书信,附玉璧一枚。信中仅八字:“天命有归,愿公勿疑。”玉璧则是当年刘焉传下的“益州牧印信”,象征正统。
刘璋捧璧痛哭,知大势已去。遂写下禅让表文,自愿退位,奉玺绶于刘备。
消息传至荆州,刘备初时推辞,三让而后受之。建安十五年正月,刘备正式入主成都,开府治事,改元“兴平”,大赦境内,封赏功臣。校尉因功勋卓著,被拜为“骠骑将军”,领益州牧,都督中外诸军事,赐节钺,位在三公之上。
然而,就在庆功宴上,校尉却悄然离席,独自登上城楼。寒风吹动他的战袍,手中仍握着那枚“断义”玉?。月光洒落,映出他眼角一丝疲惫。
他知道,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刘备称制之后,渐有称王之意。朝中大臣纷纷上表劝进,连诸葛亮也默然不语。唯有校尉始终未发一言。
一日,刘备召他入宫,屏退左右,问道:“将军随我多年,劳苦功高。今我欲上尊号,建宗庙,以安人心,你以为如何?”
校尉跪地叩首:“主公若只为安人心而称王,臣无异议。然请容臣直言??今日之天下,仍未统一,曹操尚据中原,孙权割据江东,匈奴、鲜卑虎视北疆。主公若急于称尊,恐失‘兴复汉室’之初衷,为天下英雄所笑。”
刘备脸色微变:“难道我要终生屈居人下不成?”
“非也。”校尉抬头,目光如炬,“臣愿主公先称‘汉中王’,暂摄大政,待平定中原、迎回天子,再行登基大典。如此,则名正言顺,天下归心。”
殿内寂静无声。良久,刘备长叹一声:“将军忠直如此,我岂敢不听?”
于是,刘备暂缓称帝之议,改上表朝廷,请封“汉中王”。同时发檄文天下,历数曹操篡逆之罪,宣布将以武力清君侧,迎天子还洛阳。
此举震动四方。曹操暴怒,立即调集大军二十万,命曹仁镇樊城,徐晃守宛城,张辽屯合肥,全面备战。孙权亦加强长江防线,并遣鲁肃再度来使,试探季汉态度。
局势再度紧张。
校尉深知,大战不可避免。他回到军营,立即启动战备计划。首先,命李通率军收复上庸、房陵,打通通往汉中的通道;其次,派遣细作混入关中,散布谣言,挑拨曹操与其部将关系;再次,联合马超残部,许以高官厚禄,诱其反攻凉州,牵制魏军西翼。
最重要的是,他亲自起草《讨曹檄文》,洋洋千言,痛陈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屠城戮民、僭越称公之罪,末尾写道:“吾等虽出身微末,然心系汉室,誓以一身肝胆,扫除奸佞,还我乾坤朗朗。凡我华夏子弟,无论南北,皆当奋起响应,共诛国贼!”
檄文传遍九州,竟有十余郡县官吏斩杀魏使,举城归附。就连许都附近也有百姓聚众起事,虽很快被镇压,却足见民心所向。
建安十六年春,校尉亲率五万大军,自成都出发,翻越秦岭,直逼阳平关。此关乃汉中门户,由张鲁之弟张卫镇守。初战不利,蜀军连攻三日不克,伤亡千余人。
校尉并未强攻,而是命人散布谣言,称“张鲁已降刘备”,又派人伪装成曹操使者,送去伪诏一道,言“若张卫献关,可封万户侯”。张卫本就与兄长不睦,闻讯后疑虑重重,竟于夜间弃关而逃。
校尉趁势入关,兵不血刃拿下汉中。
张鲁得知消息,悲愤交加,欲举众投降曹操。然其麾下百姓多信五斗米道,不愿北迁。法正趁机游说,言刘备仁德爱民,愿保道教传承。张鲁思虑再三,终率部归降。
校尉亲迎十里,执手相慰,待以上宾之礼。并下令保护道观经书,严禁军士扰民。百姓欢呼雀跃,称“牛将军不仅胜于兵,更胜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