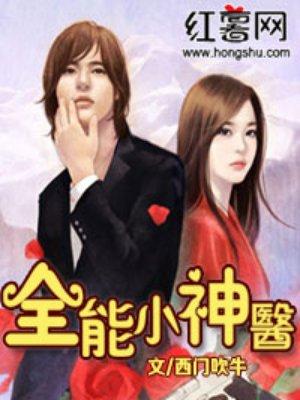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救命我被8080了无错版 > 红夜(第1页)
红夜(第1页)
出来?
等,等一下。该不会——
手机烫手似的掉在被褥上,闷咚一声响。我迅速爬起身,半跪到床尾,想要伸手把灯打开,千钧一发之际却缩回手指。我转头望向窗户。
窗型是长方形,两扇小门那样能向外推开。
休息前,我习惯性地拉上一半的窗帘。银灿灿的月色正环搂着另一半,好似从不见天日的山洞罅隙里挤进的光,一丝一缕都是充满暗喻性的蓬勃生机。
被奇异的直觉驱使着,我下了床,走过去。
轻轻拉开帘幔,勾起窗锁,谨慎地推开银白色的小门。
夏夜磅礴的热风顿时争先恐后地兜进来。它扑在眉眼、脸颊,钻入蓬乱的发丝与睡衣领口间。好像辽阔海面上一匝迷路的螺号,吹得满耳“呜啦啦”响。
我光脚踩在地板,上半身稍微探出窗外。脚踝被空调低沉沉的冷气镣铐着,可握着窗沿的手心热得一下下地跳。
与此同时,笼罩在朦朦胧路灯里的人影抬起头。
山本武穿着简单清楚的运动服。白短袖,黑长裤。
衣料单薄,宽松宽松的。晚风猎猎地一鼓,就把人吹成黑白漫画里荡着涟漪的小湖。他一只手揣在裤兜里,另一手的掌心握着手机。翻盖机又薄又长的屏幕遥遥发光,紧接着被单手盖上。
我俯视而下,看本不应该出现在楼下的山本同学神奇地刷新出现。
路灯斜晃地照亮他,像只徘徊在家门口、红枣大的幽灵宝可梦。但山本同学有影子。扎扎实实的阴影凝成椭圆形。他站在那上面,仰起脑袋眺望,昏白色的灯光让他的眼睛一霎一霎闪。
山本武就这么呆呆望来一眼。
随即,仿佛才意识到什么般,忽然变成一颗误入蒸笼的柿子。
那头发丝乌黑地耸动,脸庞红彤彤地扬起。他张嘴:“维……”继而又立刻发觉夜深人静时不宜大声讲话,连忙收声。
很快,山本同学跟小学生似的,杵在原地挥手。
不是整个手臂举起,而是掌心与肩膀齐高,小心地、可怜地、期待地挥。
我趴在窗沿,低头看他。
一时冲动涌入卧室的夜风歇落,能察觉到发丝悠悠地垂回脸侧,有点痒。而彼时被越吹越高的心跳声仍然高居不下,怦怦、怦怦,不懈地敲着脆弱的耳朵。
这是,什么情况。
燥热惘然的心音在脑袋里跌撞之际,我望着山本同学红红的脸,他紧张地抿起的嘴角,他亮晶晶的棕眼睛。蓦地,我把手臂一伸。
将敞开的两扇窗户重新合上。
惶惶暑气终于被隔在外头。我钻回清凉的卧室,又一刻不停,趿上拖鞋,拉开房门。
家人早也已经睡下了。
这幢独栋此时正是一座无边无际的静物,衬得喉咙里,胸腔下,一顿顿的脉搏响亮至极。我无声地关上门,猫着身子下楼;从二楼到一楼,走出家门,撞进月夜里穿过前院。路程极短,我却出了一身幻觉般的薄汗。
推开稍显沉重的院门,我确认地探出头。
斜对面的远处,阑干一样的路灯笔挺地矗立在转角口。灯下,则是另一杆更加笔挺的山本武型的柱子。
好傻。
人都这样,看到别人更紧张,自己就莫名平复下来。
冷静地侧身挤出门缝,我踩着拖鞋,总算敢发出一点声音地踏踏上前。越走近,那黑白色的柱子就越紧着,但紧绷半天,又不得不微微佝下脊背,垂下脑袋来看我。
“那个。”
山本武小声开口。眼瞅我靠近,跨进路灯的光圈里,他似乎连手都不知道放哪,脖颈被白色圆领衬得更红,看起来臊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