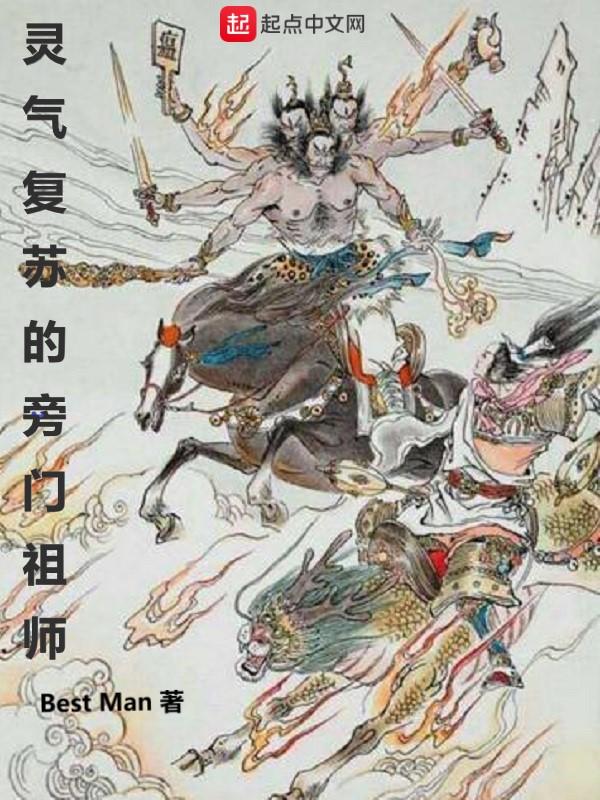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救命我被8080了无错版 > 留下(第1页)
留下(第1页)
“你,”我捂着山本武的嘴,头皮发麻地警告,“你小声一点,喊那么大声干什么呀!”
刚才精准预判,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足以居高临下地俯视坐床铺的家伙。
室内暖白的灯光打下,山本同学大半个身子笼在我的阴影里。被掐脸似的捂住嘴,他就剩一对光明磊落的双眼,泛着荔枝一样的光泽。
靠得近,我发现他的眼睛也很健康。
没有分毫的血丝,棕色的土行星的虹膜,黝黑的瞳孔在不自主地放大。
双眼皮,线条都干净利落。睫毛一眨,眼睑细微的横纹消失又出现,那是人类皮肤特有的温厚感。
男生小声地“唔唔”应答。
热乎乎的气息打在虎口与手心,我迟来地、清晰地意识到,手掌正紧贴着比脸颊更柔软的东西。
是山本同学的嘴唇。
糟,糟糕。
一时情急就冲动了。
心跳重重擂鼓,又变成一只健壮的岩羊,把后脑勺当峭壁蹦蹦乱蹬。我抿着嘴,凭借惊人的毅力而没有火速抽开手——确认他点头答应,不会大声喊,再松开。
但刚一解除禁锢,山本武就开了口。
“我喜欢你!”
“……”我不敢置信地瞪。
山本同学似乎以为是因为这也太大声。没有退缩,只又退一步:他抬起左手,拢在嘴边,几乎用气音在讲悄悄话;一面近在咫尺地朝我露出羞赧的雀跃的笑容。
“我喜欢你,”他红着脸,说得小小声,而不得不把每个字都咬清楚,“小维,我喜欢你。”
大脑突然有点缺氧,我才发现自己从头到尾没有自主呼吸。
这在以前,甚至在不久前,都是我心里最不想见到的场景。从此回不到朋友关系,不能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我知道我肯定不会接受,怎么都有理由拒绝。
逃回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卧室里,这是我最擅长的事情。
发烧容易传染。我张张嘴,好像嘴唇也和脸一样滚烫。
“……我。”
这是我艰涩的声音。
山本同学又叫了一声我的名字。我的视野像跌倒一般,从他身上滑落,撞到床角,又坠在黑色的皮鞋尖。
我要冷静。
我要冷静的时间。
现在这种情况,再待下去……
指腹与掌心仿佛还温存着谁的触感。我后退一步,鞋跟不小心踢到椅子腿,碦。我听见自己磕绊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先别管我。”
“维。小维,”男生的声调骤然抬高,“等等!”
我转过身,扭头要走。
然而,满眼望向医院锡色的房门之时,身后猛地撵来一阵咚隆当啷的杂响。像是一下翻倒或扯倒什么重物。
被这叫人心惊肉跳的动静拴住脚踝,我吓得又赶紧回头。
只见山本武整个上半身都悬在床边,拦腰垂下。右手手背的输液贴紧连细管,管子一扯,输液架顿时倾斜地往病床上压倒。不锈钢沉闷一响,磕撞在床沿。
我下意识睁大眼。
“山本君!”
笨、笨蛋吗?!
回过神时,我的身体已经快步赶回去,扶起摇晃的架子;双手一伸,把那颗忘记腿不能动、抵不住地心引力、头朝下的黑绒绒脑袋捧起来。
而还没来得及把他托回床上,一只手忽地攥住我的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