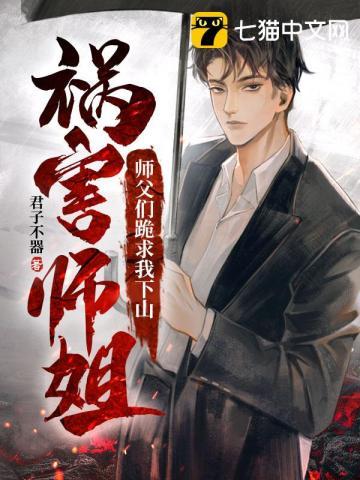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顾先生今天谈恋爱了吗? > 第 16 章(第1页)
第 16 章(第1页)
第16章
董事长办公室那场质询的寒意尚未完全从骨髓中散去,顾毓那记精准打击技术命门的阳谋又接踵而至。慕可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脚下是川流不息的城市脉络,他却感觉仿佛置身悬崖,呼啸的风声是顾毓报告里那些冰冷的技术术语构成的。
那份《数据模型重大风险提示报告》就躺在他的邮箱里,像一枚引信嘶嘶作响的炸弹。它不是恶意中伤,而是建立在严谨数学逻辑上的质疑,每一处风险提示都引经据典,数据翔实,论证过程几乎无懈可击。这才是最可怕的。顾毓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直指七寸。
“六个月的回溯测试和压力测试……”慕可喃喃自语,指尖冰凉。六个月,足以让任何创新项目胎死腹中,足以让董事会那点本就脆弱的耐心消耗殆尽,足以让沈乐轩之流找到无数个趁虚而入的机会。他等不起。
但他没有时间沮丧或愤怒。顾毓将战场选择在了技术层面,他就必须在这里迎战。逃避或诉诸情绪,只会让他输得更快更惨。
他立刻行动起来。
首先,他再次拨通了母校教授团队领军人物李教授的电话,语气前所未有的凝重:“李教授,情况紧急。我们遇到了顶尖的技术质疑,需要最强大的学术火力支援……是的,关于社区价值量化模块的核心算法,在极端压力测试下的稳定性和鲁棒性……我需要您和团队最精锐的力量,最好能联合计算数学和社会动力学方面的专家,进行一次联合攻关验证……时间?我们没有时间,但必须挤出时间!代价由我来承担,请务必帮我这个忙!”
电话那头的李教授感受到了慕可语气中的决绝,沉默片刻后,郑重答应立刻组织跨学科团队进行会诊式分析。
挂了电话,慕可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阅读顾毓的报告。他必须真正理解对方的每一个论点,才能找到反击的缝隙。报告写得极其漂亮,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站在对立面,慕可都会为之赞叹。顾毓精准地抓住了模型在极端假设下(例如社区大规模失业、公共设施突发严重故障引发信任崩塌、区域性经济危机等)可能出现的非线性崩溃风险。这些风险确实存在,任何模型都无法完美规避所有极端情况,但顾毓的报告将其放大并论证为“根本性缺陷”。
慕可闭上眼,大脑飞速运转。对方的论证建立在几个关键假设上,这些假设虽然严谨,但是否过于理想化?是否忽略了现实社区中存在的缓冲机制和自适应能力?模型的优势在于动态调整和学习能力,但在极端瞬时压力下,这种学习能力是否反而会成为不稳定的放大器?
一个个技术问题在他脑中盘旋、碰撞。他知道,这是一场硬仗,他必须在学术上和逻辑上彻底驳倒这份报告,至少是证明其风险在可控范围内,或者可以通过模型迭代快速修复,而非需要长达六个月的停滞。
与此同时,他也不能忽略其他战线的压力。
沈乐轩的骚扰变本加厉。他甚至直接给慕可的私人邮箱发了一封邮件,措辞优雅却充满居高临下的“关怀”:
“慕总,近日听闻远航内部对创新项目多有波折,深表遗憾。明珠蒙尘,实乃憾事。若远航平台束缚过甚,鄙人处始终虚位以待,资源、平台绝非问题,唯才是举。盼君慎虑,静候佳音。”
慕可冷冷地看着这封邮件,直接点了删除。沈乐轩越是急切,越证明他看好这个项目,也越证明他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向白远年施压。这既是危机,也是筹码。
内部调查虽然结论偏向慕可,但“可提升空间”的评语像一根软刺,让一些原本中立的同事开始下意识地与他和他的项目保持距离。流程变得更加繁琐,跨部门协作时,对方总会多问几句,多要几份备案。这种无形的消耗,极大地拖慢了效率。
团队士气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核心成员依旧坚定,但连续的风波和质疑让氛围有些压抑。慕可召集了一次内部会议,没有回避问题,将顾毓的报告要点(脱敏后)坦诚告知团队。
“这是我们遇到的最严峻的技术挑战。”慕可的目光扫过每一张年轻而带着忧虑的脸,“怀疑和质疑,是创新路上的常态。顾总提出的问题很尖锐,但并非无法解决。这正是检验我们模型韧性,推动它走向成熟的绝佳机会!如果我们能跨过这道坎,我们的模型将无懈可击!”
他分配任务,让技术团队全力配合教授们的验证工作,同时自己牵头成立一个临时攻坚小组,专门研究模型在极端情景下的优化方案,寻找哪怕只能将风险等级降低一点点的可能性。
“我们要做的,不是否认风险,而是证明我们管理风险的能力。”慕可定下了基调。
接下来的日子,慕可和他的团队进入了近乎疯狂的工作状态。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深夜,白板上写满了复杂的公式和推演过程,咖啡消耗量惊人。与教授团队的远程会议频繁而激烈,不同学科的思维碰撞出火花,也时常陷入僵局。
慕可身先士卒,他重新捡起尘封已久的数学功底,啃着那些艰深的论文,与技术人员一遍遍模拟测试。压力巨大,他时常感到太阳穴突突地跳,睡眠严重不足,但他不能倒下。他是这个项目的灵魂,他必须比任何人都坚信能够成功。
在这个过程中,他偶尔会想起顾毓。那个男人像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已然冰冷庞大,水下还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力量?他这次出手,是为了彻底扼杀项目,还是……另一种形式的“锤炼”?顾毓那句“不喜欢有人把我当枪使”和“你的理想国注定寸步难行”,总在慕可脑中回响,含义复杂难辨。
一天深夜,慕可还在核对一组数据,私人手机突然震动。又是一个陌生号码,但归属地显示本地。
他心头一紧,犹豫片刻,还是接了。
电话那头却是一个轻柔而略带怯意的女声:“请问……是慕可慕总吗?”
“我是。您是哪位?”慕可警惕地问。
“我……我叫林薇,是顾总……顾毓总手下数据安全组的分析师。”女孩的声音有些发抖,“我……我可能发现了一些东西,关于那份风险报告……”
慕可的心猛地一跳,他立刻走到窗边,压低声音:“你说什么?什么东西?”
“我……我不敢在公司系统里说,也不敢用公司的电话。”林薇的声音带着恐惧,“报告里引用的那组关于新港市社区动荡的基准数据,其清洗和预处理流程……可能被人为修改过参数,放大了极端效应。我……我核对过原始数据备份和最初版本的清洗日志,有细微的不一致,但足以影响最终的压力测试结果。”
慕可感到一股电流窜过脊背:“你有证据吗?”
“我……我偷偷截屏了日志对比,但不敢发出来。顾总对信息泄露查得非常严……”林薇几乎要哭出来,“我只是觉得……这不对。这不是严谨的技术态度。慕总,您……您要小心。”
电话突然被挂断,只剩下忙音。
慕可握着手机,久久无法平静。
林薇的话像一把钥匙,插入了他心中关于顾毓报告的某个疑点锁孔。是了,那份报告完美得近乎苛刻,其假设的极端情景虽然理论上存在,但概率极低,且其对初始数据的敏感性极高。如果基础数据预处理环节真的被动过手脚……
这是顾毓授意的吗?为了确保报告一击必杀?还是他手下有人为了迎合他,或者被其他势力收买,暗中做了小动作?
顾毓知道吗?如果他不知道,那说明他的团队并非铁板一块。如果他知道……那他的形象就变得更加复杂难测——一个追求技术绝对正确的人,却使用了不光彩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