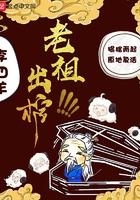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遗觉象和视觉后象的区别 > 有关易小天的讨论(第2页)
有关易小天的讨论(第2页)
“重要的是他的过去。你辖区里,五六年前,有没有发生过涉及儿童走失或遗弃的警情?尤其是棚户区拆迁那段时间。”
赵朗放下餐盒,表情认真了些,用还算干净的手背蹭了蹭下巴。
“你这一问……好像是有那么点影子。就火车站后面那片老区,拆的时候乱得很,外来户多,关系也乱。”
“好像是有过一两起报小孩不见的,但后来……好像又都说是找到了。或者家里大人说不找了,是跟另一边老人走了之类的。”
“那时候监控没现在这么发达,笔录做得也糙,好多都不了了之。”
赵朗叹了口气,身子往后,靠在了冰冷的微水泥墙面上。
“老严,你知道这种案子最难搞。清官难断家务事。有时候不是拐卖,就是家里穷,或者出了啥变故,养不起了,自己扔了,或者孩子自己跑了。你查到最后,心都能凉半截。”
“就算找到源头,那个家……可能还不如他现在这样。”
房间里一阵沉默,只有空调系统维持恒温的低频嗡鸣。
严序的手指无意识地在冰凉的桌面上敲击着,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
“社区那边呢?”他问,“那个老板娘阿珍,知不知道什么?”
“问过。”赵朗摇头,走过去打开冰箱想找点喝的,结果里面只有一排依云水和几盒成分标注清晰的蛋白棒,他悻悻地关上门。
“她也只知道那孩子好像突然就出现了,一开始抢她家对面快餐店泔水桶里的吃的,被人轰过几次。后来她看不过眼,就每天早上放一小袋,头天卖剩的东西在后门那个木箱上。”
“她说从来没听他说过话,有时候靠近点他就龇牙。问她知不知道哪来的,她也摇头,就说‘造孽哟’,别的啥也不知道。”
“街坊邻居也都这反应,都知道有这么个孩子,但谁也说不上来从哪来,叫啥名。时间久了,就跟巷口那棵歪脖子树似的,成了个摆设。”
“他不是摆设。”严序低声说,更像是对自己说,“他有非常严密的认知地图和行动轨迹。他的世界很小,但秩序井然。”
“秩序?管翻垃圾叫秩序?”赵朗失笑,但看到严序毫无笑意的表情,又把笑憋了回去。
“行吧,你说秩序就秩序。那然后呢?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就这么天天隔着一截看他?给他投喂画册?”
“这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啊。总不能让他一辈子住报刊亭吧?”
这正是问题的核心。
未来走向。
严序沉默了片刻。
他看向窗外,楼下是车流不息的繁华街道。
霓虹闪烁,却与他,与那个报刊亭里的孩子,都隔着一层冰冷的玻璃。
“公安的程序性处理,对他无效,甚至有害。”严序冷静地分析,像在做一个案件推演,尽管背景是他这间不像家的家。
“强制救助,他会激烈反抗,过程会给他造成严重心理创伤。就算成功送进救助站,以他的情况,只会被当成有严重行为问题的精神障碍患者隔离起来。”
“他赖以生存的感知和反应系统,在那种环境里会彻底崩溃。结果很可能不是救助,而是毁灭。”
赵朗没反驳,只是表情沉重地用筷子戳着米饭。
他见过太多类似的例子,制度是僵硬的,而人是复杂的,尤其是易小天这样的。
“社区的非正式网络,”严序继续道,“是目前唯一支撑他生存的基础。但它是脆弱的,不稳定的。依赖于个别人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