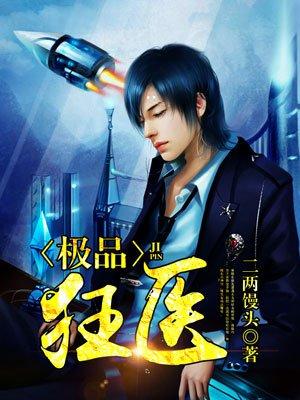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重生之我要拿下肖赛冠军 第一个老师 > 第15章 悲怆(第3页)
第15章 悲怆(第3页)
林哲远的眉微微挑起。
他注意到江临舟此刻在处理右手旋律时的控制:音色没有泛光,却保持极高的一致性。
每一个音符之间的力度与连结都处理得干净,不失形,不溢响。
左手内声的切分节奏踩得极稳,没有丝毫犹豫。
这不是从容的稳,而是经过计算与训练后的稳定,像是反复推演过数十次。
他的呼吸控制得极准。
不是为了情绪流动,而是为了维持结构脉络的平衡。
第二次主题回归时,江临舟略作调整,延音稍长,力度更沉。
不是表达,而是重新压了一下重心。
唐屿察觉到了。
他没有动笔,目光却紧盯在右手旋律上。
并非重复,而是转向。
不是铺陈,而是推进。
进入过渡段前,左手切分节奏略为干涩,像是刻意“抽空”了一拍,让听觉陷入极短的真空。
徐柏年眼角一动。
“收得狠。”他在心里咂舌,“这是在清场。”
随后的音区突变。
右手旋律跃入高音区,江临舟没有将其拉开为明亮音场,反而继续压着节奏,让音符在高处紧绷,近乎不见回响。
像是一根拽得笔直的细弦,维持着与地面的拉力。
最后一段回归,速度略缓,旋律处理得克制至极,甚至不留余音。
没有柔情,也不作结语。
只是将这一段作为一种“架桥”,把乐章架在两段主结构之间,维持重心,不许下坠。
唐屿微不可察地颔首。
林哲远合上笔。
徐柏年不动,只是目光略略偏向了键盘左侧。
江临舟的手指依旧停在原处,仿佛最后一颗音还悬在空气中未曾落地。
他缓缓收回手势,几乎无缝地,转入了终乐章。
第三乐章开始。
他没有在这里寻找爆发感,也没有刻意制造情绪转折,而是维持着前两章建立起的张力框架,在急速节奏中完成结构闭合。
段落转换干净利落,所有节拍都踩得精准有力。
他没有试图“点燃”什么,只是稳稳走完每一步。
这是一次收束,不是高潮。
当终止和弦落下,空气中没有多余的余响。
江临舟松开手指,起身,站在琴前。
评委席静默无声。
他的演奏,结束了。